
編者按:王國維先生曾經提出過膾炙人口的“治學三境界”之說👈🏽,中國現當代著名哲學家和哲學史家馮契先生亦對其治學方法作出過評述。本期《周一談哲學》為大家帶來馮契先生對王國維先生哲學思考的闡釋🥗,希望大家在兩位大家的交互中收獲自己對於哲學治學的特殊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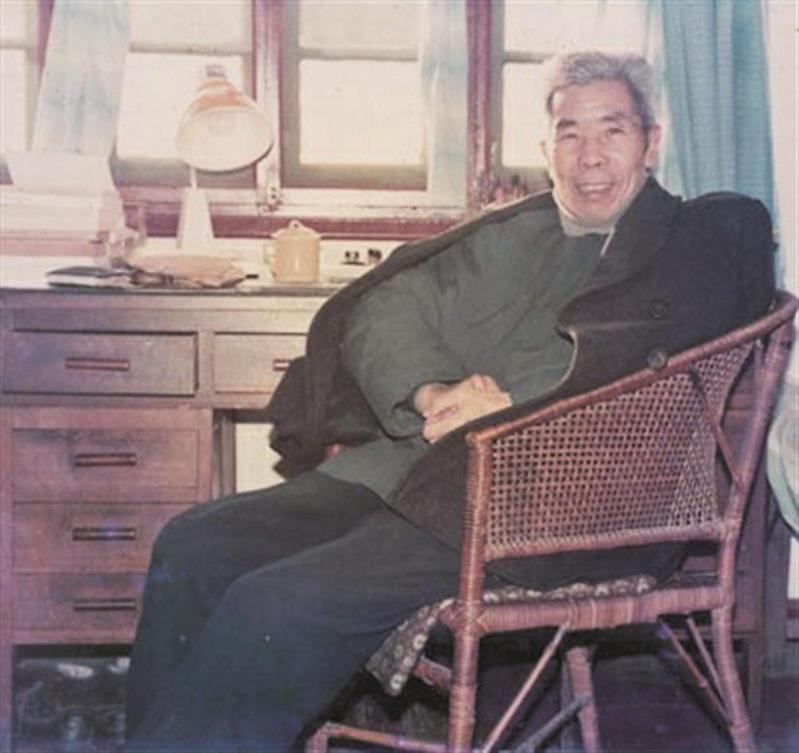
哲學學說的“可愛”與“可信”
王國維是一個對哲學很有興趣的人。他確實認真地鉆研了哲學👼🏽,然而他在三十歲時所寫的《自序》中說: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靜庵文集續編,自序二》)
王國維對當時西方傳來的兩種哲學思潮🧈🐚,作了上述的評價☠️,反映了他內心的矛盾。他說的“可愛者不可信”,是指康德🀄️、叔本華哲學。他以為康德、叔本華的哲學是“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純粹之美學”。他說的“可信者不可愛”,是指象嚴復所介紹的實證論的哲學。實證論者通常在倫理學上主張快樂論🧓🏽👩🚀,在美學上主張經驗論◻️。王國維作為科學家,他傾向於實證論,因為實證論是同實證科學相聯系的🕵️♂️。但在感情上,他覺得叔本華的非理性主義和唯意誌論更可愛🧑🏻🔧。
經驗論和先驗論的對立,實證論與形而上學(包括非理性主義)的對立,這是西方近代哲學史中令人矚目的現象🕵🏿♂️,也是中國近代哲學史中不容忽視的事實⚱️。正是這種對立,使王國維深切地感到可愛與可信的矛盾👨🏻🌾,產生了思想上的極大苦悶。這當然同他個人的氣質有關,但也有著深刻的認識論根源和社會根源👩🏿🔬📰。兩種哲學思潮的對立是近代的科學與人生脫節🐶、理智與情意不相協調的集中表現👩🏻🦽➡️。同時🍡,哲學本身具有意識形態和科學的兩重性:作為意識形態,一種哲學學說總是反映一定社會集團的要求,使這一集團的思想代表覺得“可愛”;但它只有作為科學知識的概括🎠🍕,才令人覺得“可信”。顯然👨❤️💋👨,站在人民立場上來看那既具有人民性又具有科學性的哲學學說,“可愛”與“可信”是可以達到一致的。但王國維既尊重科學,又固執學術超脫政治(即超脫當時維新派與革命派)的立場,所以便感到無法解決這個矛盾了💇。
王國維始終未能解決他所謂的“可愛”與“可信”,即非理性主義與實證論之間的矛盾。不過,既然矛盾的方面存在於一個人身上🌤,當然會互相作用🏊🏿♀️、互相滲透👴🏿。剝去非理性主義與實證論的哲學形式,我們將看到👭,在王國維的性格中,既有對思辨哲學(他所謂“純粹之哲學”)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觀的知識”的實證精神。正因如此,他能用實證精神對‘概念世界”進行反思,並從哲學的高度來總結治學方法,使得他在分析批判傳統哲學範疇和自覺運用實證方法兩方面作出自己的獨特貢獻。
對傳統哲學範疇的分析批判
王國維所寫的《論性》🖥、《釋理》、《原命》等文🫶🏻,其基本立足點雖然沒有超出康德🚻、叔本華哲學,但他通過中西哲學的比較,對中國哲學史上的“性”、“理”🏋🏿♀️、“命”等範疇作了系統的考察和分析,是頗有實證精神的。特別是《釋理》一篇↪️,對程朱之所謂.“理”作了分析批判,確實提供了新的東西。
王國維認為理有廣狹二義📆。廣義的理即“理由”:就自然界說,一切事物必有所以存在之故,即理由;就人的知識說🐫,一切命題必有其論據🏊🏻、亦即理由,所以充足理由律為“世界普遍之法則”與“知力普遍之形式”。狹義的理即“理性”,就是“吾人構造概念及定概念間之關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種也”📵。
他認為普遍概念本是叢具體事物中抽象出來的,如果忘記了它的來源,以為離開具體實物別有一種實在性;如把“有”視為離心物二界的“特別之一物”,那便成了形而上學的概念了。“理”的本義是剖析,“物之可分析而粲然有系統者皆謂之理”↔️。但是,朱熹卻把‘理”形而上學化🦸♂️,說“理即太極”,並以為“天理”可以體認、“自證”等等🧎♂️➡️,其實不過是培根所謂種族的偶象、康德所謂先天的幻相罷了。這種幻概“不存於直觀之世界,而惟寄生於廣莫暗昧之概念中”(同上),是求真理者必須加以深察明辨的。
科學的治學方法
王國維的治學方法則可以說是自覺地貫徹了他對名實關系的哲學觀點、既肯定“名生於實”,要求從事實材料出發⛹🏼♀️,又強調抽象的重要,要求從哲學的高度來考慮問題、他繼承了清代樸學的傳統⛹️,也汲取了西方實證科學的精神、他的哲學思辨能力幫助了他,使他的治學方法超越前人而有以下幾個特點:
壹
他治學很善於運用比較法,熔古今中西於一爐。陳寅洛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講到👨🏻🌾,王國維治學的方法可概括為三條,這主要是從比較法說的🧟。第三😌,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第二,“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第三產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王國維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實物與文字記載互相釋證,他研究邊疆地理💆🏽、遼金元史,是幸中外古籍進行互相補正👄,他寫《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這些著作,則是把西方傳來的觀念同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料進行參證。他和梁啟超一樣,比起前人來,眼界確實要寬廣得多,他能看到地下實物、外國典籍🧑🦳,能夠拿外國人的思想觀點♖,同中國固有的思想資料進行比較研究
貳
他有比較自覺的歷史主義態度🏟。歷史主義可以上溯到浙東史學。不過章學誠講“道不離器”、“時異而理勢亦殊”,他所謂“道”,“理”是比較籠統的一般。王國維已受了歷史進化論和實證科學的洗禮,他說研究歷史“在求事物變遷之跡而明其因果”(《國學叢刊序》),這就是要求比較具體地揭示歷史事物的演化規律。在他看來,歷史上的一切學說◀️,一切製度,風俗🎋,皆有其所以存在與變化的理由,“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製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於一時之故,其因存於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同上)雖然王國維有唯意誌論傾向,但他以為在經驗世界中,自由“不過一空虛之概念”👃🏿。他說:“一切行為必有外界及內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於現在必存於過去,不存於意識必存於無意識,而此種原因又必有原因,而吾人對此等原因但為其所決定而不能加以選擇”(《文集續篇·原命》):所以👩👧👦,在現象世界、歷史的領域,他是個決定論者。當然👨🏼⚕️,他的歷史主義也有其局限性,如把周初的政治製度和典禮的變革,歸之“皆為道書而設”,把元代雜劇發達的原因🤶🏿,歸之“完初之廢科目”等👩🔬,這說明他不懂得唯物分觀,不可能揭示出歷史演變的根本原因🎭。
叁
他強調要從個別與一般的統一來把握事物。他說:天下之事物🔴✈️,非有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雖一物之解釋,一事之決斷,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雖宇宙中之一現象,歷史上之一事實,亦未始無所貢獻。(《國學叢刊序》)就是說,要從曲和全,即從個別與一般、部分與整體的統一來把握事物🚷。一方面,要深知宇宙人生真格💅🏽,就要有哲學思想來作指導🦻🏼,另一方面🧑🏼💻,他認為宇宙間任何一個現象☂️、任何一個歷史事件下不分大小、近遠,統統都要力求把握其真實。一方面把握全👨🏽🔬,一方面把握曲🎹,歸納與演繹相結合🦐,並作系統的歷史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所考察對象的“所以存在之由與其變遷之故。他這樣自覺地運用個別與一般、歸納與演繹相結合的方法,顯然已吸取了西方實證科學的精神,超過了乾嘉學派。
不過,所謂把握全,由全以知曲🧑🏽🍼,歸根結蒂是要把握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相的哲學。從這方面說,他的方法論有其局限性🔛👨👩👧👧。因為他不懂得唯物史觀,他受康德哲學的影響,以為因果律是主觀的,斷言“理之為物,但有主觀的意義,而無客觀的意義😶🌫️。(《釋理》)。他認為🎅,不論是作為知識的普遍形式〔範疇)的理由,還是作為構造概念的知力的理性,都是主觀的📇。這種先驗主義觀點削弱了他的方法論的科學性。
但王國維能從哲學的高度來講治學方法🍟,用實證精神來分析傳統哲學概念🧚🏿♀️,正說明他在某種意義上已把“可愛”與“純粹哲學”與“可信”的實證知識統一起來了。
本文選自《王國維的哲學思想與治學方法》,原載於《河北學刊》1987年第6期😷,作者:馮契🤙🏻。文章部分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