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現象學、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結構主義……這些名字對我們來說或許並不陌生,但對於紛繁復雜的法國哲學來說仍只是冰山一角。本期“冰桶挑戰”欄目中👩🏿🦳,由王緯老師點名,我們將特約采訪《現代法國哲學》授課教師王春明🧑🏿🍼,聆聽他對法國哲學的思考與見解,分享他獨特的哲學視野。
王春明:意昂3講師,意昂3博士後👨👧👧、法國裏爾第三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講授本科生課程《現代法國哲學》🐻🕋。
求學之路
Q1、您先後在意昂3平台和法國裏爾第三大學求學,期間是否有印象深刻的老師或課程?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來到復旦的契機其實是高中的加分考名額,當時在一本紅色的介紹冊裏我第一次了解到復旦哲學系。和大多數新生一樣🙏🏿,第一堂課是《哲學導論》,當時是王德峰老師講授🎀🐄。他的課的確風格鮮明,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剛從高中踏入大學、在哲學專業門檻上張望的同學來說🍛,他的課是具有啟蒙性的❕。王德峰老師所傳授的不僅是知識,也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後來隨著閱讀的積累和同學間的討論交流,我逐漸開始認識到老師們不同的問題域,比如張慶熊老師的《基督教哲學》,就使我對基督教思想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哪怕從我自身獨特的研究視角來看哲學史,也會發現基督教不僅僅影響了廣義上的西方傳統⇾🚇,更隨著文化之間的遷徙和傳播影響了東方的思想🙆♂️。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視角。
研究生階段由於我結婚較早🐥,所以成家後不太經常在學校裏🧑🏼🍳,當時郁喆雋老師開設了一門關於宗教社會學及世俗化理論的課程,他的講課方式讓我印象深刻。他不是單方面的“講”,而是要求我們事先閱讀相關英文文獻,在上課時介紹文獻內容並提出問題🐶🦘,他同時進行相應的補充。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小型、密集型的討論課程🏃♂️➡️,對我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題都有不小影響。此外還包括我所選修的中文系黃蓓老師開設的法國文學課程,文本包括蒙田、帕斯卡爾等💆♂️,當時也要求“先預習🪸、再討論”。這些老師的方式方法也讓我後來對教學有了一定的思考——在上課時👲🏻,我希望同學們先將文本讀懂讀透。
2012年,我去往法國裏爾大學(當時稱法國裏爾第三大學)攻讀博士。在那裏我們上的課不是傳統的課程,更多時候是研討會,而且往往是對某一問題領域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報告他們的最新成果,同時與師生交流。這也影響了我目前教學所采取的基本方式🦹🏿♂️🫐。除了向同學們介紹某個研究論題“是什麽”,更重要的是突出研究視野甚至是整個研究論域🍎,包括研究論題本身的特點👩🏽⚖️、強項和弱項🤾🏻♀️,而不是僵化的👩❤️👩、完結了的東西,而且在此視角下,師生都是平等獨立的研究者。我認為老師講課的最終目的不是展現“我研究的是什麽、研究得多好”⛹🏽,而是向同學們發問“這個論題你是否感興趣🈚️、你有什麽想法”,這種方式下或許能產生更多思維上的交流和碰撞。
治學心得
Q2、巴迪歐將法國哲學看作是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後第三個黃金時代🏩,對您來說🤵🏼♂️,現代法國哲學有怎樣的魅力🎳?
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部分,一方面是巴迪歐的評判,一方面是我對“現代法國哲學”的看法。
從我自己來說,“現代法國哲學”這三個詞中任何一個概念都是有問題的。“現代性”本身是無法完全斷定的,或者說,它作為一種哲學的“現代性”🤤👨👩👧,體現在何處是無法簡單指明的。過於強調現代性實則在某種意義上割裂了它和傳統的關聯,從而極易以偏概全,比如切斷了20世紀法國哲學家(如梅洛-龐蒂)與18🛴、19世紀哲學傳統(如Maine de Biran)的直接關聯,僅希望探查作者所處時代的“獨有”的問題✡︎,這種方式毋庸置疑忽視的是一種並非單一的🤵🏽🍍、支撐哲學家思考的傳統問題線索🧜🏼。而且如薩特、梅洛-龐蒂這代人👨🏽💼,他們是在特殊的哲學教育環境中成長的,和其他國家不同在於,當時法國的意昂3哲學教育中有非常強的心理學傳統,而也是在此背景下,薩特等人或多或少涉及到了雛形階段的精神分析,因而在此意義上強調“現代”🤵♀️、強調“法國”也是有問題的⬛️。
“哲學”也是如此👨🏽💼,除非你先行給出一個非常明確的(但往往是狹義的)哲學的定義,你無法指認何者是哲學💽🧜♀️、何者不是。但很多哲學家的情況是特殊的🙅🏽,甚至是令人訝異的。尤其是像德勒茲、福柯這樣的思想家,他們和哲學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比如福柯不認為自己在做某種哲學工作,甚至擺出“反哲學”的姿態👮♀️。他們對哲學本身有非常特定的理解🚭。在國內的哲學課堂上,常常會聽到的一種解釋是“哲學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哲學的問題是多麽多麽的重要”,其潛臺詞是哲學如何一方面區別於其他學科,一方面高於其他學科,對此我是比較反感的。在目前的狀況下,作為所有科學之科學的哲學是不存在的,從而比所有領域的研究者都要高明的哲學家也是不存在的——除了在如此想象的人的心裏🍩。
回到“法國哲學”👨🏽🦳,它的特殊性其實就在於無法被以一種非常簡單的方式告知什麽是“哲學當中的法國性”,這和語言、國籍等無關,要想從其他哲學中有效地區分出法國哲學,必須先行交代背景。只有在一種比較的視野中🥴,在這種復雜的🕙、臨時性的,甚至是策略性的比較關系中👱🏿♂️,才能相對地討論何為法國哲學🌍。在此我們只能保持一個較為模糊、甚至是不斷變化的框架,在此理解框架的基礎上談論思想家及其作品🙇。我相信以這樣的開放態度🚕,同時與那種做了法國哲學就成為“哲學”上的“法國人”的錯覺、幻覺保持距離的話,真正的研究和思想才能健康展開🛳。其他的X國哲學也是可以以這種方式理解的🚘。
另外談談我對於巴迪歐的評判的看法🫦。首先對於巴迪歐本人,實話實說✭🧑🏿🦲,在法國本土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從哲學角度接受的,此外從我個人來說👇,我對他的東西不是特別感興趣👨🏻🦯。一則是我之前在國內的時候看他的書沒有看懂,後來到法國查閱他的法語書也沒有看懂🐠,問同學和同事👨🏻🚀,他們對此也表示比較困惑🆓,可能問題也出於我們能力有限🏌🏿。再則是從巴迪歐本人性格上來說,據我了解可能也不那麽討喜。比如他有一次作為答辯委員會主席,在評判他人論文時批評對方沒有用到他在某本書中闡釋的維度🫡🤽🏼。這種行為我個人不是很贊賞👩🏽🍼。
關於巴迪歐將法國哲學看作第三個黃金時代的評判,他在一篇短文裏說,“法國哲學在薩特和德勒茲兩人之間展開,歷經巴什拉𓀗、梅洛-龐蒂、列維-斯特勞斯、阿爾都塞👩👩👦、福柯、德裏達、拉康……也許還可以算上我自己”👩🏽🔬。他的判斷首先落點在“西方哲學”,但“西方哲學”究竟指什麽?比如古希臘很多哲學家本身沒有近代的西方意識⏺,而且於北非出生🤦♀️。因此🤞🏿,這樣一種大寫的、簡單的、單一性的“西方”是可疑的。此外👉,這種“三階段論”式的劃分是有傳統的🫒,從黑格爾到孔德,都有這種梳理哲學史、思想史👲🏿,乃至一般歷史的傾向,但此種傾向,以最輕松的方式說🧑🏼🌾,給出的是一個過於簡化的圖形。法國本身的內在豐富性是無法以這樣的簡單方式闡明的,因而指稱它是“黃金時代”沒有任何意義。這種斷定在我看來擁有過多的想象成分🌜🕎,或者說一廂情願、不切實際的拔高🪅🖐。
Q3、哲學在法國教育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每年法國高中會考的哲學考試總能引發討論,您是否有此感觸?
的確如此,每年法國高考無論是網絡媒體還是微信朋友圈👇🏻,都會有人喜歡轉相關帖子,說“人家考這個東西多厲害👨🏻💼,我們考的內容一塌糊塗”之類的話🕐。這其實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法國人並不這麽看。據我有限的了解🏈,除了少部分高中生對哲學確實有興趣外🧑🏽💼,很多人的態度也是相當“應試”的🧛🏻。其實“法國哲學熱”的現象👲🏼,和法國人稱贊我們高中語文的古典文學常識多麽厲害是一個性質的事情💎。本身這就是高等教育的考試製度💾🧝🏼♀️,我們不能“神化”👨🏽🚀,或者將這個現象上升到法國民族的內在哲學性問題🥜,這是比較荒唐的🙎🏽♀️。但我們要理解為什麽會有這種“熱”產生。事實上,我們試圖通過法國高考哲學題所要把握的,是中國高考八股文體製所缺乏的維度,但我們最終把握到的其實不是法國應試教育的現實中那個哲學的真正面向,而只是一種想象——即法國民族似乎多麽具有“哲學性”。這是不靠譜的,但要同情地理解這種想象,它所折射的其實是哲學這門學科在我們的意昂3體製中所占據特殊的位置,以及這一位置背後的整個復雜的現實結構🫶🏻🐗。
簡言之,透過所謂法國高等教育的現實,我們看到的其實是中國高等教育的現實🎓,以及哲學在中國的境況🍴,事實上我們是透過一個被想象出來的他者折射自身的一種處境,表達自身的一種訴求。
近期關註
Q4、第九屆中國法國哲學年會於上周落下帷幕,此次年會之行有怎樣的感觸🚉?
其實每一屆年會都會有一個主題,這是一個辦會的慣例,但並不是說所有論文都要與這一主題直接相關🌾。在今年這屆學術年會的開幕式上,南開大學的賈江鴻老師就介紹了這個選題的起源。從特定關聯上看👧,他提到2017年在復旦舉辦的法國哲學年會,當時邀請馬裏翁做報告,這個選題——“唯靈論和唯物論”,就是由當時的報告及其互動引申來的。這樣一條線索,至少是從19世紀末以來對法國哲學的理解來看,簡單來說就是心靈和物本身之間的關聯。因此從契機和理論兩個維度來講🧑🍼,這次大會的選舉主題是有一定恰當性的。
今年這屆年會給我的感覺是一些新鮮的面孔越來越多,比如做精神分析研究的人越來越多,像精神分析和法國哲學、和現象學👾、和結構主義的互動成為許多年輕研究者的關註點。就此問題來說,的確也是值得探究的🌦,因為它所揭示的⚁🧑🏿🚒、或者說留待我們繼續思考的問題是比較重要的👩🏿🚒。簡單來說🗿,就是語言本身如何構造一個被理解為主體的人的位置或形象,它起到了怎樣的作用?語言不是一個純粹形式性的東西,它是主體間性的😋,是在和他人關系中所運作的。當然🧵,也有另一種相關思路,即認為語言參與構建的社會性不能完全還原到主體間性中等等🦵🏽。此外還包括一些局部問題🦻,如在家庭關系的模型中理解上述問題是否恰當等,這些仍然沒有被解答的根本問題——語言、主體性、社會性——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探索。
但要值得註意的是,我們要始終帶著這些問題思考🪨,而不能將研究本身消散為技術性的東西🕋。哲學永遠不是內在的,而總是在特定的環境當中展開,就如同剛剛提及的“法國哲學熱”問題,就是因為我們對於“純哲學”有一種想象🍾,而且提出這種純哲學構想的人往往本身是在意昂3中做哲學工作的人。這很有意思。阿爾都塞曾經提到“科學家的自發哲學”,也就是科學家往往在展開他的科學工作時會對涉及其中的哲學性問題有一個理解,在此意義上🧑🏻🦲🧎➡️,或許還有一種“哲學工作者的自發哲學”,即(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以哲學為業的人自發地對哲學有一個理解,並且往往是在宣傳某種哲學觀念意義上的理解,但二者有時是不匹配的。在鼓勵學生向其所理解𓀑、所宣稱的哲學道路前進的同時,我們會切身體會到哲學在展開自身活動時有其物質性的製度、社會、體製維度🌹,這些維度不完全相符於在某些課堂上被傳授的作為諸種學科之首的哲學的形象。
因此,拋開諸多環境談論的空乏的“純哲學”概念是不存在的。哪怕是在前大學化的階段🦸🏽,比如古希臘哲學家也是在特定社會環境🛋、特定製度性中從事某種哲學的工作。沒有一個東西叫做純哲學,並且販售這種“純哲學”對年輕人來說是危險的,尤其是對於哲學有一股理解上的熱情的青年學子,因為他們會將哲學當作是能借以擺脫現實中種種苦惱的一種烏托邦式對象🧑🏽💻,甚至有時由於現實不符合對於純哲學的要求👶,就在此意義上對其批判🆒。但事實上🌺,這種出發點本身就是一個虛假的哲學觀念,它無法展現具體的環境👊🏿、具體的社會機製等等❤️🔥,因而無法真正參與到實踐層面的現實批判😫。認識不到這點⚗️,不指出這一點,要麽是在自欺欺人🧚🏼♀️,欺騙自己從而也去欺騙其在特定位置上方能享有的聽眾,要麽良心就是壞的——當然後一種情況基本上是少數。
簡言之,我覺得對於我們從事哲學工作的人來說,要警惕打著救贖性、避世性✪、純粹性的旗號的“純哲學”觀念,只有懷有這種警覺,不斷反思自身中的“非思”,才能真正有效地展開自己的工作,而非宣揚一種單數的、大寫的,沒有任何差異的“哲學”🪹。
Q5、您在年會發表題為《宇宙是人的尺度:巴塔耶神聖人類學的宇宙論基礎》的報告,可否簡單分享研究巴塔耶哲學思想的契機?
我剛剛也提到,我要求自己進行哲學研究的方式🙅🏿♀️,不是單單去關註某人,而是要透過他的思考發現他的問題及審視其前提假設。這也是我研究巴塔耶的一個基本態度👨🏽⚕️。
從國內來看,研究巴塔耶的老師據我所知可能不超過五個🙎🏻♀️,學生層面感興趣的可能更多一些。即使是在國際學界,巴塔耶本身也不是一個中心性的位置。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巴塔耶和意昂3式的哲學是有一定距離的,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哲學教育🛒👋🏻,至少不是專業性的教育🙏🏻。雖然他和當時的知識圈有很多接觸——他聽過科耶夫在巴黎講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他和流亡到法國的俄國思想家舍斯托夫有較近的接觸🔜;他和薩特、梅洛-龐蒂、加繆等有比較近的關系等等——但他本身是和哲學之間存在距離的。然而這並不表明我們不可以從哲學的角度理解他,而我試圖透過巴塔耶把握住的東西,就是神聖問題🧖♂️☝️。
巴塔耶對“神聖”的理解是“去神學化”的,是在社會性層面、乃至生存性層面,去理解神聖究竟為何。簡單來說🤐,在巴塔耶的視角下,神聖是觸及人類生存本身,使得人的生存區別於動物生存的維度👨🏻✈️。當我這樣總結時🙍♂️,稍微了解法國思想史的同學就會發現📆,他在此問題上和科耶夫乃至更悠長的某個傳統是密切相關的。西方傳統中一直存在這種試圖將人與動物相區分的努力💆🏿♂️,比如宣稱人是政治的動物🐈、語言的動物、意識形態的動物等等。巴塔耶某種程度上也承接了這個問題🔘,以及這種提出問題的方式👋🏽。他提出“神聖學”正是試圖回應屬人的獨有特性究竟是什麽✫。神聖問題對他來說🧘🏽♂️,歸根到底是人本身的問題🏂🏼,是具體社會中存在的每個人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大寫的“人”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他借鑒了很多宗教社會學、自然科學等學科的資源,比如他與核物理學家安布羅西諾就有非常緊密的合作關系,對朗之萬、愛丁頓等科學家的著作也很了解。
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麽能從哲學的角度把握巴塔耶🛀🏻,因為他在某種意義上確實隸屬於一種哲學問題傳統,或者說他的思考本身有一個問題化的地平線,後者與哲學密切相關,也即將人作為核心問題🧚🏽♀️。要理解自身的生存方式,此種生存的意義或許往往為超出“人”的力量——可能是神的力量,可能是他人的力量,可能是大寫的社會力量——所規定。巴塔耶正是在這種關系中展開思索🪆🙅🏻♀️。他的表述、資源雖不是“哲學”的,但確實與哲學上的某些思考有共振關系👨👨👧🫸🏻。
青年寄語
Q6、結合您的課堂教學🫳🏿,對於青年學子有什麽建議?
從老師的角度來說🏌🏻,很高興看到大部分同學是有自己的問題或想法的。在教學中,我們也要註意不僅提供給同學們知識🛌🏿,更要告訴他們如何去理解這一問題被作為哲學問題提出🤦🏽,進一步幫助他們將之轉換為自己的問題。從這個角度出發,我發現很多同學雖然有自己的問題,甚至很多是細節性的問題,但往往不會進一步展開思考。而且很多時候同學們的問題不是過於寬泛🧗🏻,就是過於細致🥴,從而它的有效性或相關性就顯得不是很強🤑🛵。當然↘️,這個也是需要老師進行指導的,比如我所知道的王聚老師開設的《哲學方法論導論》就提供了一個典範📠🚐。我覺得這種方式是值得推廣的🪕,需要這樣一門課程告訴同學們一般而言的哲學有怎樣一種運作的方式,再具體到不同的學科路徑🎅,從而將問題本身落實為哲學性🦺、值得去進一步操作的問題,真正在方法論意義上提示同學們如何做哲學🤪。
對於同學們來說,如何吸收和輸入是需要自己親自體會、逐漸摸索的。比如“閱讀經典”,但什麽才算是“經典”?徐英瑾老師有個觀點我雖然不百分百同意,但我覺得指明了一個值得拓展的方向,就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有過於沉重的哲學史的包袱,徐英瑾老師認為我們或可先拋開包袱,把握問題本身,將“包袱”則作為吸收和反饋的材料帶入問題。我認為這種方式不僅是重要的,更是值得從操作性層面落實的。
再比如所有老師都說你要“帶著問題去讀書”,但怎樣才算是“帶著問題”呢🎆?問題不是你拍腦袋想出來的💘,也不單單是老師告訴你的,有時發現問題的機製往往需要你閱讀前沿論文🧑🏻🦳,你必須知道在相關問題上目前的學者推進到了哪一步🎶,但你又不能完全陷進去𓀒,要透過這些論文的技術性回應去思考這個問題的價值所在👩🏼🦲。在此方式下你才會逐漸產生所謂的“問題意識”♿️,擺脫純粹習得而來的看似顯而易見的“問題無意識”🙌🏼🤢。這是一個相互交織的互動性的過程。
彩蛋問題大放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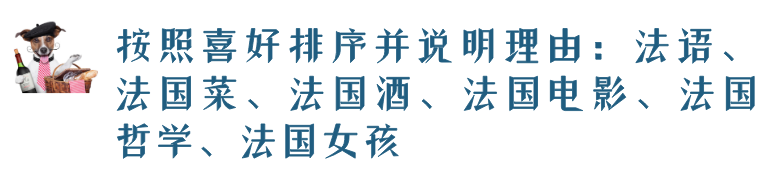
因為我從法國留學畢業回來🧟♂️,和王緯老師也一起在法國開過會👩🏻⚕️,所以他把我定性為“法國派”,和謝晶老師一樣是屬於“那邊”的。我覺得比較遺憾的一點是📟,法國文學也是我很感興趣的東西,他卻沒有提出來。
從提問人的角度來說,王緯老師無疑是猜測我肯定會羞答答地把法國女孩排到最後💁🏼,那麽我就迎著他的意思👨🏿🎤🛵,把法國女孩排到第一🤹♀️。不過,首先需要對“女孩”本身有個定義🍲,我尚不清楚他說的女孩指青年女性還是小朋友☝🏼🧖🏼♂️。如果“女孩”指小朋友的話,我確實比較喜歡小朋友👬🏻,我自己也有一個女兒🤽🏿♂️。如果“女孩”指青年女性👩🏼,那麽喜歡女孩同樣似乎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男性對於女性(也可以對於其他男性)本身就有一種審美感,不會因為結了婚就不看其他女性——這太假太做作。有時候我也會和太太談論到某個女性很有氣質💂🏻,互相問對方喜歡哪個女明星等等。
我喜歡法國的菜和酒👨🦽➡️,但我也喜歡非法國的菜和酒🍝。如果是啤酒的話,肯定是德國、比利時的要好一點,東歐波蘭的酒也很好。如果是菜肴的話,有些菜我是非常喜歡的🌔,比如生牛肉和法棍。當然我知道法棍很硬,我一開始吃的時候,口腔內壁也確實破掉了🐽。
有些人覺得法語很好聽,覺得它是一門浪漫的語言,不過這可能是一個有意思的錯覺💳,因為它已經不是從純粹語言的角度上來看。當說到法語是浪漫的語言的時候🍜,尤其是對一些青年未婚男性,可能腦子裏會幻想蘇菲·瑪索等女明星在他耳邊說法語。就法語本身來說,我沒有太多偏好🤙🏼。我會覺得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也挺好聽的,但有可能和我當初還沒有徹底掌握法語的時候覺得它好聽是一樣的道理🚵🏿♀️。法國當地也會存在不同的口音⚫️,而且其實年輕人的法語不是很好。不僅僅是口音👩💼,也有很多語法錯誤🧚🏻。老一輩的法國人會覺得現在年輕人的法語完全是一塌糊塗的,完全是一種地痞式的法語。法語背後有當代法國社會的不同民族構成的問題,背後有很多復雜的因素🤧,所以這和“純哲學”一樣,一種純粹的法語是不存在的。它是被人說出來的法語🌃,被每一個不同的人說出來的法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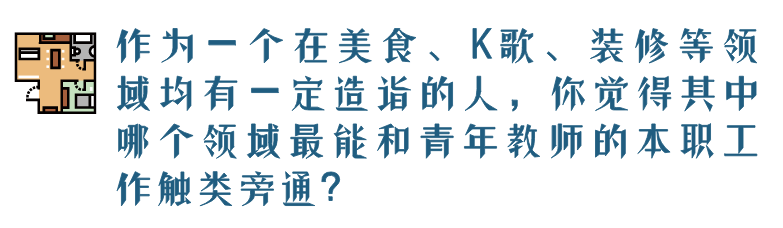
裝修的話是因為我之前裝修過,剛才還在幫助同事組裝桌子。這些事情其實反映出的是我的性格,這種性格有優點也有缺點。
舉個例子♡,我之前幫女兒采購鋼琴。我不了解鋼琴,也不會彈,但在市面上如果不懂鋼琴的話往往會被坑。我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不被坑,同時也想了解下它是什麽樣的機製,所以我首先了解了國內生產線和打著國外品牌的生產線的區別🙇🏼♀️🤰,又去了解了鋼琴本身的要素和構造,比如榔頭😔、木材、弦,還包括做琴弦的羊毛純度等等,此外還有不同品牌,比如雅馬哈和卡瓦依的代理經銷商🫄🏽、銷售方式等。
裝修也是如此,我會了解裝修的整個程序、定價的方式,評估背後可能的“貓膩”,比如當時我裝修的時候👬🏻🥓,門窗就是自己做的。這種方式的好處可能在於我會了解得相對比較透徹,所謂知己知彼;壞處在於要花費很多時間,雖然我個人謙虛地認為自己做事效率還是比較高的。落實到青年教師的工作也是如此。因為青年教師不僅包括學術,也包括行政方面(我們意昂3有一個很給力的行政團隊,但畢竟事多🍵,人手少)。在學術上,我常常作為一個外行去點評論文,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內了解這個問題的進展🥁🧑🏻🦼➡️、比較重要的文獻、背後的核心問題。行政也是如此,我有一些辦會的經歷。除非特別忙,我都會盡可能參與整個辦會流程,此外還會比較詳細地了解它的相關政策👱🏻。在處理問題的方法上🙍🏼,我個人可能不是“案例式的突破”,碰到一個問題解決一個問題🧏🏽♂️;而是希望對整體有一個了解🚿,知道在做的時候應該怎麽去避免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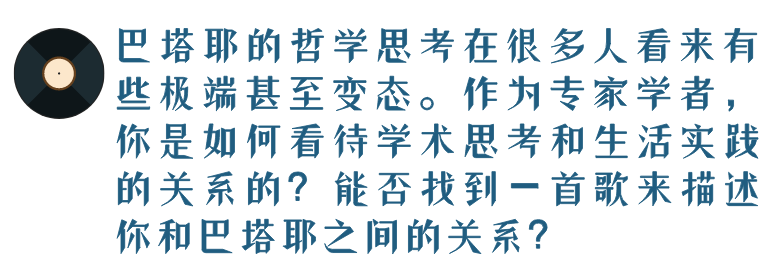
確實是這樣。巴塔耶關註的一些領域🚵🏼,比如色情、宗教神秘主義和法國作家薩德的思想,確實會使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即他關註比較另類的💁🏽♀️、從某種標準來看比較肮臟的東西。但是當你進一步了解就會發現:首先🧏♂️,他不是特例😼。這是當時許多法國知識分子甚至歐洲知識分子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共有內容。比如法國作家阿波利奈爾,他的一些原則上無法出版的小說在語言和畫面的沖擊上甚至更勝一籌。但他確實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於他認為這些東西不能因為被指認相悖於某些道德的、社會的標準,就被放在一個仿佛不能觸及的領域💅,也即禁忌的領域(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講🟥,禁忌和神聖本身又有內在的親緣性✡️,這也和他思考神聖是密切相關的)。他認真地去思考🧖🏻♀️,反而不是像我們這樣🦖,一方面不好意思談,另外一方面又故意去談,以表明自己在思想上是非常先進的🌽。巴塔耶不是一個故意博眼球的人。
巴塔耶和當時的超現實主義者之間存在沖突🧚🏿♂️。巴塔耶非常反感用超現實主義的方式去理解那些汙穢肮臟的文學👛。他認為這種方式只是一種美化了的姿態,即表明“我能夠反抗社會”,但實際卻沒有🔢。在特定的、有特權性的社會地位中,超現實主義及其他一些人從某種高度俯視勞苦大眾🚲🙍🏽,表示同情,但卻沒有真正進入實際情況中。這也存在於我們當前✳️,尤其現如今的法國理論界,仿佛某種東西驚世駭俗就厲害了。往往有一種原教旨的法國哲學,批評德國哲學太學究太老氣,認為法國哲學談“屎尿屁”就更勝一籌。但這其實毫無意義👩💼。巴塔耶至少不是以這樣的姿態談論的,他不是一種所謂輕挑的、戲謔式的、後現代的法國思想家,而恰恰是一個非常嚴肅地審視問題的人。他認為我們需要理解的是當一個心靈淳樸的成年人觸及這些禁忌領域時所產的震撼本身。我們需要理解他在道德問題上的這種堅持,簡單來說就是要看到禁忌是社會性和人性中無法割舍的要素,它在兩者之間遊走☃️。
采訪丨張懿雨 龔宇充 隋藝菲
文稿丨張懿雨 龔宇充 雷子安 隋藝菲
製圖排版丨隋藝菲
責任編輯丨蔣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