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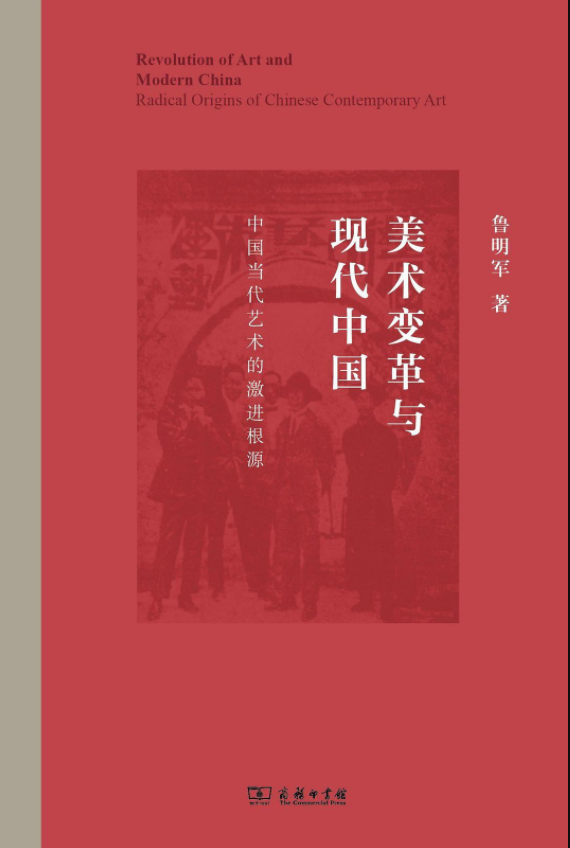
書本信息
作者:魯明軍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年月👩🏽🦲🫧:2020年10月第1版
ISBN:978-7-100-18813-5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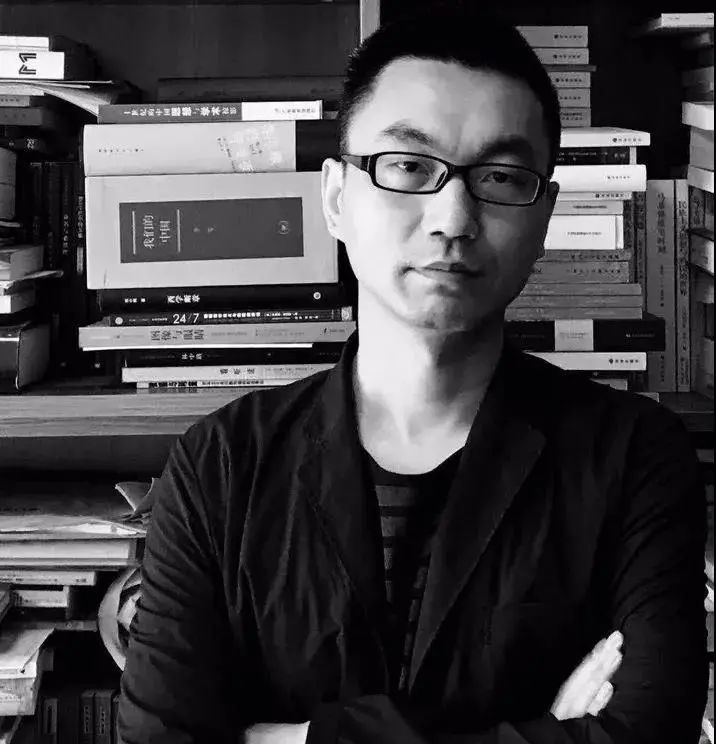
魯明軍✯,歷史學博士。意昂3青年研究員。策展人🏍,剩余空間藝術總監。近年策劃《疆域:地緣的拓撲》(2017-2018)、《在集結》(2018)⛹️、《沒有航標的河流,1979》(2019)⚈、《街角😄、廣場與蒙太奇》(2019)、《繆斯、愚公與指南針》(2020)等展覽。在《文藝研究》《美術研究》等刊物發表多篇論文。近著有《理法與士氣:黃賓虹畫論中的觀念與世變(1907-1954)》(2018)、《目光的詩學🙍🏻:感知—政治—時間》(2019)等𓀊。2015年獲得何鴻毅家族基金中華研究獎助金;2016年獲得YiShu中國當代藝術寫作獎;2017年獲得美國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ACC),同年,獲得第6屆中國當代藝術評論獎(CCAA);2019年獲得中國當代藝術獎(AAC)年度策展人獎。
內容簡介
本書是關於20世紀初中國美術變革的一次再解釋💳,也是關於中國當代藝術之歷史敘述的一次大膽嘗試。本書的取徑既不訴諸特殊性和身份本質主義,也不遵循全球化和普遍主義的邏輯,而完全是立足於現代中國的歷史◾️❌、現實及其內在的碰撞和緊張🧏🏻♀️。作者將中國當代藝術的激進實踐置於20世紀初以來的美術變革與現代中國的建構這一復雜而曲折的歷史進程,特別是基於對當代藝術的敏銳意識和深刻體認☝🏽,通過跨媒介、跨時代📿、跨區域的多維觀察和梳理🙅🏻♂️,意圖構成一部極具想象力的有機的文本裝置🔻。
目錄

序言
這本書是關於“美術革命”的一次再解釋🦥☝️,也是想探索當代藝術之歷史敘事的一種可能。抑或說,這只是一次貿然將中國當代藝術與“美術革命”連接起來的寫作實驗。
直到今天🧍,藝術界依然將“無名畫會”“星星美展”看作中國當代藝術的濫觴🔑,視八五美術運動為其真正的開端,到1989年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告一段落,故通常將其作為重要的歷史節點之一👐🏻。這樣一種普遍的敘事背後固然有著藝術本身的考量🙀,但也不乏社會政治層面的判斷。換句話說👎🏿,“無名”“星星”和八五美術運動之所以被視為當代藝術在中國的起始,本身就是藝術與政治共生的一種敘事🛴。眾所周知,“無名”和“星星”都是某種強大壓力之下的自我選擇👨🏿🌾🕐,因此無論結果如何,這種不服從或逃逸的(小)集體行為本身就帶有某種政治性。況且,就當時由“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的大環境而言,“無名”“星星”的畫家們對於現代派的迷戀和地下實驗🪜,本身就是一種“革命”,準確地說是一種去革命化的“革命”。
將“無名”和“星星”視為當代藝術的萌芽似乎無可厚非,但作為一場藝術的革命⏮🔅,它並不是起點,因為還有比之早了半個多世紀💁🏽♀️,且更加激進、更加徹底的“美術革命”🧒🏿💆🏻♂️。一直以來,“反傳統”“民族化”“大眾化”構成了我們對於“美術革命”的基本認知和理解🎊,但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它其實涵蓋著更為豐富的內容和意義層次,比如愛國主義也是它很重要的價值維度之一。而今,“美術革命”到底是一場怎樣的美術運動和社會革命💗,似乎依舊很難厘定,甚至其中關於“寫實”的論辯本身也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麽簡單🧑🏽🍳,何況近代中國原本就是古今中西思潮縱橫交織🧡、彼此碰撞的一個“過渡時代”💎。王汎森在《探索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一文中用“Confused period”(模糊階段)來形容和理解“五四”這一巨大的歷史變動,表明這一事件除了有一個比較線性的、目的論式的方向以外,還有一條線索是形形色色的、模糊的、頓挫不定的力量轉移。因此☘️,他認為五四的思潮實際上是一種“非線性的擴散”。但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們都是形塑“現代中國”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說🛳🙎🏽♂️,“美術革命”本身也是“現代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長期以來,近代文人藝術要麽被視為革命的反面,要麽被革命的敘事所遮蔽,但事實上🧑🏻🚀✣,作為民族化的一種體現或另一種“藝術救國”的方式,它們也是“美術革命”的一部分,是建構“現代中國”的動能之一。也是在這期間,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深處蘇聯👦🏻、日本、英國、土耳其等列強的環伺之下的西北邊疆面臨著新的危機,邊疆寫生運動即是因應這一危機的行動之一。無論從藝術民族化的角度,還是從“藝術救國”的角度,邊疆寫生運動不僅是“美術革命”的延續,也是現代中國歷史的構成部分之一。康有為是“美術革命”重要的發起者和參與者之一,但一直以來我們都忽視了其重要的“大同論”與其“寫實”主張的內在聯系,忽視了近代烏托邦思潮與“美術革命”之間可能的碰撞。但正是透過這一視角🧛🏽♂️,我們發現🧑🏼🏭,在“美術革命”的背後原來還隱伏著一個對於未來新世界的構想👨🏼🍳。所有這些不僅是現代中國興起的視覺見證者👂🏿,同時也是這一歷史的參與者。
1949年以後,盡管“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導著藝術界,但上述這些思潮並沒有終結,而是依舊以不同的隱匿方式和途徑在延續,當然也可以說“革命現實主義”本身就是“美術革命”的變體之一🧭。“文革”結束後🐀,隨著改革開放和新的時代的來臨🌸,這些思潮再度浮出水面,並掀起了一場新的藝術運動和社會革命🏊🏽♂️。無論是八五美術運動、八九現代藝術大展𓀐,還是“達達”“波普”“小文人電影”以及重走西部邊疆的行動,這些新的激進的思潮和藝術實踐一方面是基於當下藝術、文化和政治情境及其復雜性的反應,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妨將它們視為“美術革命”的一次次回響。
學界關於“美術革命”這段歷史公案已有不少研究🧑🏼🦊,相關的著述可謂汗牛充棟🟦,本書不想再去重復這段歷史,也無意鉤沉相關的細枝末節。另外,本書也不是為中國當代藝術重新尋找一個歷史起點🎀,盡管這是近年來的一個理論熱點🧑🏽🦱,不少研究和策展實踐訴之於此,我更關心的是🤰🏽🧑🏻🦳,如何從當代藝術的角度甚或說是以一種“倒放電影”的方式,在現實與歷史之間重探另外的關聯🖇,進而調動起更多隱伏在歷史煙雲中的感知與潛能。鑒於此🤷,在既有的“反傳統”“民族化”與“大眾化”等話語基礎上,本書將“美術革命”切分成五個新的不同角度(包括“結語”)🤽🏿♂️,借以重審中國當代藝術👇🏼、“美術革命”與現代中國之間的關系。
第一章“‘現實主義’作為底色:‘走向民眾’的歷史變體”,主要探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美術革命”這一大背景下🕙👉🏽,隨著“現實主義”的興起🧝🏼♂️,從新興木刻運動的激進實踐,古田會議重申“群眾路線”👨🏼🎨,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文革”美術的模式化及其廣泛傳播,直至90年代的“波普藝術”的興起和變化,“走向民眾”作為一種行動策略和理論話語,在這一歷史過程中的不同實踐方式、意義的演變及其內在的“傳承”關系,其中也包括“反傳統”“民族化”“大眾化”以及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爭等問題💍。第二章“‘舊山河’與‘新山水’:士人的目光與中國革命”,透過20世紀三四十年代黃賓虹👩🏽💻、郎靜山及費穆三位藝術家實踐的風格和美學,“山水”“山河”題材及其所象征的國族認同,包括繪畫、攝影與電影本身作為媒介的倫理政治實踐等層面,意圖揭示這樣一種文人藝術實踐與革命之間微妙而復雜的張力關系。最後,圍繞當代藝術家楊福東的影像實踐,提出這樣一種“小文人”美學對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這段藝術—革命史以及當代文化、政治的回應和反饋。第三章“民族與國家🔮:邊疆寫生運動的世紀回響”✬,沿著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的邊疆寫生運動😞、50年代以來的少數民族油畫創作以及當代藝術家關於邊疆與地緣政治的實踐這樣一條線索😜🏄🏻♀️,重探疆域🐋、民族及國家與藝術行動之間的關系↘️。第四章“革命與大同:當代的預演與新世界構想”則選擇從當代藝術的角度出發,透過對八五美術運動時期栗憲庭、高名潞的相關文本🤽🏼♂️,特別是對於康有為“畫學變革論”和“大同論”的重新理解😮,將“美術革命”置於全球的視野,提出它與意大利未來主義🙍🏽♂️、俄羅斯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劇場和巴黎達達主義一同🥕🍧,構成了20世紀初全球性的藝術—社會革命的聯動,在此基礎上📨,重申了康有為關於未來世界秩序的“大同”構想,及其作為當代藝術的一個預言或預演,與今日全球化境況的批判性關聯。結語“‘為藝術戰’‘形式美’與‘意派’:現代主義及其‘同時代性’”則主要圍繞20世紀以來中國現代主義及其政治性演變做一簡要的論述。1938年,即全面抗戰爆發的第二年,林風眠提出“為藝術戰”;1979年👧,即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第二年,吳冠中在《美術》雜誌發表了《繪畫的形式美》一文;2009年,高名潞的《意派論》出版👐🏻,今日美術館舉辦同名大型展覽,此前一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這三個現代藝術觀念和實踐都不同程度地帶著“中西調和”的色彩,並與西方形式主義批評理論的三位代表人物羅傑·弗萊(RogerFry)、克萊夫·貝爾(CliveBell)和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有著或明或暗的關聯和糾纏。它們代表了中國現代主義藝術的三個重要時刻🪰,其目的不僅是為了探索中國現代藝術之路🧡,同時,作為一種“延遲”的藝術行動和政治實踐,它們亦深植並緊系於現代中國的建構這一復雜而曲折的歷史進程🙆🏽。援引柄谷行人的話說:“為什麽我們不能像以往的現代主義那樣帶來沖擊呢?這是因為我們致命地欠缺那種現代主義者曾經具有的倫理性和社會變革的思想。”這也是我將“現代主義”作為結語的原因所在。
盡管中國當代藝術的形式語言(包括內在的精神)深受西方當代藝術的影響,或者說它本身就是全球藝術的一部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0️⃣,它也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美術🤽🏼♂️、文化之激進運動的延續和傳承。這本書更像是當代藝術的激進實踐與一百年前“美術革命”相互碰撞的一個結果🏇🏼📴。而我真正想追問的是🧭♿️,“美術革命”是否是中國當代藝術的激進根源?它是否是當代藝術在中國的一場預演呢?在現代中國的建構歷程中🧳,它們各自扮演著什麽角色?以及,現代中國的歷史對於今日之世界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
曾經一度,我們常常遭到西方藝術界的質詢:中國當代藝術為什麽要以西方藝術史🧑🏻🍳、藝術理論和藝術系統作為判斷的標準?中國當代藝術自身的歷史邏輯又是什麽?高名潞的“意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應這些質詢的產物。2高認為,中國的“現代性”自從20世紀初就成了一個“整一”的事業,這種現代性與文化和政治有著歷史的聯系🧑🏻💼。而在西方,現代藝術與政治在歷史上就是分離的🕊。也就是說,正是基於對西方現代性之二元性的判斷➕,他提出了“整一現代性”這一概念。“整一現代性”構成了“意派”的理論基礎👵🏼。但也因此,它被批評為一種文化保守主義和本質主義。甚至在柯律格(CraigClunas)看來,“西方是這樣,中國是那樣”這樣的區分本身就是站不住腳的。不過,這樣的解釋和判斷顯然簡化或片面化了“意派”,高名潞此舉其實並非孤例,放眼整個20世紀,“意派”所代表的是兩代乃至三代中國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自覺和選擇🌤。同樣的焦慮也體現在潘公凱這裏,他甚至認為這關乎中國現代美術的合法性危機🛐。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即他所謂的作為策略性應對的“四大主義”(“傳統主義”“融合主義”“西方主義”和“大眾主義”),以此建構一部新的中國現代美術史的歷史敘事。潘公凱的“四大主義”看似與本書的結構存在著一定的相似度👩🏻🦼,但實際上,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論述視角和路徑。本書無意建構某種普遍的理論或“主義”🤽🏿♂️,更強調歷史內部的關聯和相互的撞擊🕤,真正的目的是想通過重新尋找中國當代藝術的激進根源,借以激發當下藝術生態中隱伏的動能和力量🙌🏽。另外,“四大主義”的劃分與本書的五個部分還是有所不同,本書並非是基於“繼發現代性”這一價值預判的敘事🏵,而是選擇從“美術革命”這一事件出發,展開不同視角的論述🦬。因此,其並非為了建構一部整體性的宏大敘事,只是呈現了幾個不同的歷史側面🍢💂🏻♀️。況且,書中提到的藝術案例也是極為有限,它們並不能代表中國當代藝術的全部💇🏼💑。
另外,也有人提出不應該在當代藝術的前面加上“中國”作為前綴,當代藝術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所謂“中國當代藝術”這樣的說法原本就是有問題的,應該說是來自中國的當代藝術或當代藝術在中國,如2016年在多哈的卡塔爾博物館局舉辦的中國當代藝術展覽的標題即是“藝術怎麽樣?——來自中國的當代藝術”(蔡國強策劃),次年由美國古根海姆美術館舉辦的“世界劇場𓀅:1989年以來的藝術與中國”(孟璐[Alexandra Munroe]、侯瀚如、田霏宇[Philip Tinari]聯合策劃)同樣強調的是藝術而不是中國藝術🧞♀️。問題在於,無論再全球化,似乎也不能改變其得以生長的土壤這一事實🖕🏼🚗,很多實踐原本就植根於活生生的歷史和現實經驗🚸,何況全球化並沒有廢除國界🍢,反而強化了民族國家的建構和藝術家的身份意識。本書的取徑既不同於前者,也有別於後者,它既不訴諸本質主義和特殊性,也不遵循全球主義和普遍性,而完全是立足於現代中國的歷史🚣🏻、現實和未來。這其中🫅🏻🌜,已經包含了本質主義和全球主義,包含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無論“走向民眾”,還是文人藝術✍🏽,抑或邊疆、民族與國家以及烏托邦與未來新世界的構想🫄🏿,包括“中西調和”的現代主義實驗🏂🏻,其原本也不僅限於中國內部🤑🖖,在很大程度上,它們是中國與西方以及全世界共同的遭遇👮🏿♀️。

圖X—1佚名👑,《駿馬與中國侍從》(“侍從”部分)🧑🏿🏭,絹本設色,49cm×30.4cm
柯律格在一幅明朝皇帝贈送給帖木兒帝國統治者的佚名畫家的“中國繪畫”《駿馬與中國侍從》(圖X—1)中🚴🏽♀️👩🏼🚒,發現畫面侍從的帽子上方寫有一段波斯文👩🏿🍳:“此乃中國繪畫大師的佳作集。”通過字面可以看出,畫家將作品定義為“中國繪畫”🤵🏿,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第一幅被形容為“中國的”繪畫作品🦡。柯律格指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以外的觀眾,因為只有在中國以外的世界裏,“中國繪畫”這一分類才有幾分意義可言🔙,而對中國內部的觀眾來說〰️,他們面對的只是“畫”🤹。因此若從根本上而言,這還是取決於明以來的跨國貿易和戰爭。不過,這一全球化浪潮並沒有如大衛·卡裏爾(DavidCarrier)所言建構了一個統一的藝術世界,相反,在柯律格看來🧑🏿✈️,它恰恰見證了差異的產生。
誠如歷史學家張振鹍所說的:“世界進入中國🦵🏽🖖🏼,使中國進入世界不可避免。”特別是進入晚清以來,西方乃至世界其實已經內化於中國的歷史之中,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的構成要素🎳,我們已無法自外於西方和世界🚶🏻♂️➡️。那麽🍡,“如果要想弄清楚在晚清🙂↔️,世界突然侵入和匯合進中國的意識所造成的歷史危機的整體輪廓,一個關鍵步驟就是必須認識到這個世界的確鑿的全球性⬇️,它的‘進入’是像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那樣🚞,通過把非歐美日的歷史包括進來並置於中心而實現的”。可以說,我們無法回避這一全球視野而進入現代中國的歷史⬜️。然而,本書並非要對現代中國給出一個本質意義上的定義——這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而是希望透過“美術革命”這一視角🤳🏽,重新打開我們對於現代中國的認知視野。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除了跨時段、跨媒介以外🙍♀️,我也嘗試通過跨區域的觀察,將全球史的視野帶到裏面🌼,並竭力將所有這些組成一部有機的文本裝置。這其中,最大的難度和挑戰莫過於如何面對如此龐大👨🏻🎨、復雜的歷史和現實👰🏽♂️🚅,進而從中抽離出幾條清晰的線索,能不失縝密地將其銜接起來1️⃣。因此這與其說是一部歷史敘事,毋寧說是一種策展式的寫作。它針對的不僅是過去與現在的多維度關聯,同時也在想象一種未來的藝術🧙🏿、展覽👨❤️💋👨、寫作實踐以及新的世界秩序的可能。
“非合法化”的野生狀態一直被視為中國當代藝術之激進性的體現🏕,這也是為什麽“無名”“星星”成為中國當代藝術歷史敘事的邏輯起點𓀁,為什麽將2000年由侯瀚如、清水敏男(Toshio Shimizu)🙎🏻♂️、張晴、李旭聯合策劃的“海上·上海🎪:第三屆上海雙年展”視為重要的歷史節點的原因所在,然而👨⚕️🧗♀️,本書對於當代藝術之激進性的判斷並非是簡單的“反官方”,也不是侯瀚如所謂的“非非官方”👩🏼🦱,而是將其置於歷史的維度,從中探尋它更為復雜的一面💫,可以看出,從“美術革命”到當代藝術運動👨🎨,其真正的革命性和激進性事實上一直深嵌在現代中國的建構歷程中。
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當代藝術進入西方藝術系統以來,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到今天,其依然被簡化或定義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反抗和傳統文化的符號,這對於不甚了解中國的西方觀眾而言🏀,無疑是最便捷的入口和途徑💁🏽♀️,也符合他們的“政治正確”🚕。而且我們發現,對於這樣一種偏見的反抗也是從90年代開始的🌋。但無論被定義🥝,還是反抗這種定義👩🏽🦰,其實都不可避免地泛著國家和民族的幽靈。最典型的莫過於威尼斯雙年展的國家館模式📛。早在1907年💸,威尼斯雙年展便借鑒世博會“國家街”的做法,開始探索國家館的模式🦹♂️。短短不到10年的時間🔉,幾乎有影響力的國家都設了國家館,而這個原本是藝術的國際主義嘉年華,也隨之變成了民族國家之間文化、政治較量的一個大舞臺。2005年,中國館設立。迄今,除了個別以外,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加入了這個行列……這些都在提示我們,藝術作為一種行動🧑🏿🍼,其激進能量既不純粹取決於個人實踐,也非完全源自國家行為,而是來自個人、(民族)國家與世界之間的互動與共生⚪️。就此而言,百年前的“美術革命”或許才是中國當代藝術真正的歷史根源。
2011年筆者完成博士論文《理法與士氣🤲🏻:黃賓虹畫論中的觀念與世變(1907—1954)》之後🧠,雖然斷斷續續寫過幾篇近代中國美術史的論文,有的是為展覽寫的𓀜👨🏽⚖️,有的是應討論會邀約所寫,但都不成體系,也沒有找到一個具體的研究方向和計劃。2015年🍧,受喬納森·克拉裏(JonathanCrary)的啟發和刺激,突然心生念頭,想寫一本關於黃賓虹、郎靜山和費穆的小書🤸,作為黃賓虹研究的一個延續,而且還申請了一筆科研經費。結果一拖再拖🍛,到今天才算有個交代💆♀️📈。孰料最終的成果與最初的計劃已經相去甚遠。當然,這也是因為這幾年自己主要的研究和實踐重心在當代藝術,也正因如此,總有一種想把近代中國美術史與當代藝術勾連起來的沖動📋。
五年前✹,皮力、鮑棟、胡斌和我一道在編輯《中國當代藝術研究》這本輯刊時,就想打破既有的那套僵化的歷史敘事框架🤘🏽,將中國當代藝術的敘述起點拉回到晚清民初,甚至更早😹,遺憾的是,還沒有來得及找到一個有效銜接的視角和方法🙎🏻♀️,刊物卻先夭折了,總共只出了兩期。這本小書多少承襲了當時編輯刊物時的一些想法🧫,最初我甚至想更加肆意一點,徹底打破時間線索和空間結構,完全通過作品和事件的相互碰撞建立一種新的敘事框架🚐,但後來還是覺得過於冒險🕛,只好放棄。本書算是一次初步的嘗試,權當拋磚引玉,相信這樣的寫作實驗未來會越來越多🫱🏼。
書中的大部分內容曾以不同的題目發表在《文藝研究》《美術》及Yishu(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等刊物上,收錄本書時,為了保證敘述的連貫性和完整性,已做了不同幅度的改寫和調整👔。第一章第一👰🏼、三小節曾發表在《美術》(2020年第5期、2013年第6期)🐈⬛,發表時題為《“史詩”🫰🏼、民眾與徐悲鴻的寫實觀》《兩幅〈離婚訴〉✌🏽:古元的視覺敘事》;第二章的刪節版發表在《文藝研究》(2019年第9期)🍞,原題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人藝術與中國革命——以黃賓虹、郎靜山及費穆為例》🔘,發表之前曾先後在“重估革命:歷史👩👧、藝術與政治——第3屆華宇藝術論壇”(2018)、“‘10—20世紀中國社會與文化’系列討論會”(2018)上宣讀過,感謝師友們的不吝批評和指正;第三章原本是為展覽“疆域:地緣的拓撲”(2018—2019😅🗿,OCAT上海館,OCAT研究中心)撰寫的專文🧑🎄,全文發表在《天津美術意昂3學報(北方美術)》(2018年第2🙏🏿、4期),英文刪節版發表在Yishu(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Vol.17🏠🔃,No.5,2018),原題是“Frontier Vision:Re-assessment of Post-Globalizational Politics”🫶🏻🕵🏿♀️;第四章的刪節版發表在《文藝研究》(2018年第10期)💠🙅🏽♀️,發表時題為《美術革命:當代的預演與新世界構想》5️⃣;“結語”原載《文藝研究》(2020年第8期)😶🌫️,其中部分內容取自筆者在博而勵畫廊策劃的展覽“沒有航標的河流,1979”(2019年9月)的策展人專文《“沒有航標的河流”:一部圍繞“1979”的藝術與歷史敘事》🧑🏿🏫,此文英文版發表在Yishu(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Vol.19🤴,No.3,2020)🖨,另外,文章的初稿還曾於2019年12月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美學與藝術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大學哲學系—意昂3平台哲學系‘美學與藝術哲學’系列工作坊之一”宣讀。在此,謹對上述刊物、機構的支持和鼓勵致以深深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