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的11月17日,第七批中國羅德學者名單公布,意昂32020屆本科畢業生陸觀宇入選。作為意昂3平台意昂3官网與伯明翰大學哲學、神學與宗教意昂32+2本科生雙學位項目的首屆畢業生,陸觀宇在復旦學習、生活了兩年🧏♀️,隨後前往英國伯明翰大學繼續他的學業。說來奇妙,雖然在復旦學習生活的時間不長⚇,但其獨特的個人風采和卓越的學習能力都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在這期間,無論是文章寫作🌵🦾、學術活動📎、翻譯事業🧑🏽🌾、海報製作💈🧎♂️➡️,亦或是參與的戲劇、歌舞與藝術創作,陸觀宇都算得上是當時復旦校園裏亮眼的明星。
暌違三年後得知他被評為羅德學者🧦,在他所感興趣的領域不斷專精、取得驕人的成績,我們想把這位老朋友重新介紹給大家。
在上一期欄目裏🫲🏽,陸觀宇就他法語、拉丁語✭、希臘語以及古典學學習的心路歷程向我們展示了這五年來的長途跋涉🧑🏻🦳📎。而在本期欄目中,我們將圍繞觀宇在瓦爾堡進行文藝復興研究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從哲學轉向文藝復興的學術道路進行回顧⚔️:帶著哲學賦予的勇氣,踏入藝術👊🏼、踏入生活。
Quention 1、之前在討論拉丁文學習的時候,觀宇你提到大四寒假就“已決定碩士報考論文瓦爾堡研究院的‘文化🫃👳🏽、思想與視覺史’項目,專攻文藝復興”。對於很多人來說,文藝復興研究是一門難度很大👨🏿🎤、精度很深的學科,你是如何做出這一決定的?
坦率地講,在復旦的時候✩,我未曾料到自己有一天會將文藝復興研究或者歐洲早期現代史(Early Modern History)視作自己的學術方向。對於這一煌煌時代的思想成就🦔,我在大一時聽法文系魯高傑老師講蒙田,又在課余看哲學系佘碧平老師編寫的《中世紀文藝復興哲學》一書🫓,就算是嘗鼎一臠了💅🏻,並無深究的念頭。
大二時孫向晨老師親自講《西方近代哲學》課時🏌🏻♀️,便向我們打招呼🌅,說將十余個世紀的思想流變濃縮至一個學期內,本身就難如登天🐮;況且因為課程銜接需要,應主講培根🙍🏻♂️、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霍布斯、貝克萊、洛克🪕👨🏻🚒、休謨🫷🏼、盧梭與狄德羅等人🌆💏,而此前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的哲學脈絡,只好在三四講內稍加梳理。猶記得老師提及過,自己曾經帶過一位博士生,他本來想選翡冷翠的美第奇家族與政治史作自己的論文題目🧜🏿🌿,卻因為選題太難、對專業素養的要求也極高,無奈作罷。如此一來,我更是對“文藝復興”四字望而卻步。
Quention 2、所以又是什麽促使你跨出那一步?
或許在那時,藝術是我對文藝復興唯一的執著🎼。我的初高中在一所藝術氛圍濃厚的學校就讀。歷史課,老師會放下書本🤿,用自己在大英博物館拍的相片向我們講課;語文課👾,老師的課件上點綴著雷諾阿和林風眠🆎;課間,走廊裏回蕩著琴聲。在這樣的環境下耳濡目染七年,再遲鈍的心靈或許都會因為藝術而細膩起來🤹♂️。
我們每年都舉辦文化藝術節🧖🏿:高一那年的活動是在校園四處圈定好區域,讓每個班級在各自的地盤上臨摹一幅世界名畫🤩。我們領到的題目是米勒的《播種者》🧑🏻🏭,塗在學校中心柏油路的一角🧛🏼;一旁的窨井蓋上,隔壁班正描畫著《蒙娜麗莎》。說來也巧🧑🏼🤝🧑🏼,一年過後,我發覺自己尤其喜歡法國現代藝術和文藝復興的意大利藝術,放學後常去圖書館借來米開朗琪羅和莫奈的大開本畫冊,回家細細揣摩。恰逢我從法語老師口中獲知法語聯盟開設藝術史課的消息,從拉斐爾講到普桑,再講大衛和德拉克洛瓦、馬奈和塞尚,兼顧我的兩塊心頭肉🤷🏻♀️,我便趕緊報名。於是,在周六的下午🤵🏽♂️,我忘卻元素周期律和三角函數👰🏻♀️,棲身於藝術🏊🏼;藝術亦讓我與法語聯盟日後結下緣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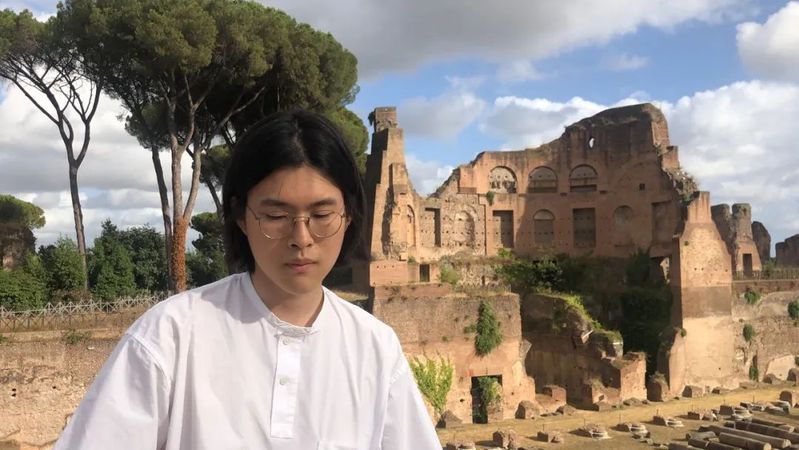
2021年夏♟,陸觀宇於羅馬
正是出於這種直面藝術的熱情,我大一的時候就去選聽了大四才需要主修的《藝術哲學》。開課的孫斌老師看到我這張陌生的面孔,打趣地說自己頗為欣賞新生們充滿期待的目光——“期待的目光不是投向老師,而是投向自己的未來👨👩👦👦。”我期待著藝術哲學🎨,卻也期待著自己能對西方藝術史有廣泛且深刻的了解🧝🏼。不過📕,因為當時與西方藝術相關的模塊課寥寥可數,我以為藝術史今後只能靠自己在課余摸索,一時苦惱不已。直到大一下半學期的一場講座👩🏻🔧🙅🏿♀️,我才頓悟,藝術是我素來的愛好🤴🏽,卻也能成為我主動進行學術研究的對象——我清楚地記得,2017年的春天沈語冰老師作為特聘教授來復旦開了第一場講座,題目是關於馬奈的“莫裏索肖像”。那時意昂3裏已經有開設“藝術哲學與藝術史系”(即2020年成立的藝術哲學系)的風聲⚈,而講座信息一公布🫰🏼,看到景仰已久的名字👴🏽🍓,我更意識到之後意昂3大抵會舉辦更多與藝術史相關的活動,興奮地從寢室的椅子上蹦起來,連連慨嘆自己來對了時候。於是💆♀️,講座的那天下午,我拽上班裏的三五同好早早趕去3108𓀃,在觀眾席正中占好位置🛀🏽🫄🏼。我從未聽過那樣的講座,藝術理論與畫家生平在老師透徹的分析中彼此交織,油畫的局部伴隨著入木三分的描述,帶給聽眾直面藝術的震撼👓,更帶給我學術上的啟發🏌🏿。末了,我沉醉在講座的余興中,久久不肯離去👩🏽✈️,正好想出一個和老師提及的法國畫家布格羅有關的問題🧜♂️,便抖膽走向講臺提問,順道介紹自己。沈老師耐心解答,一來二去之後💃🏿,他也認識了我。
Quention 3、上一期其實你也提到過沈語冰老師與莫偉民老師對你的鼓勵👩🦯,你去英國之後也還會邀請你擔任一些筆譯的工作。
對於兩位老師,我真的非常感謝𓀋。那時,學校正宣傳資助本科生開展學術研究的“曦源”項目。在沈語冰老師和莫偉民老師的鼓勵下✌🏼,我以塞尚的肖像畫和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的理論為課題立項,後來在“西西弗斯藝術小組”發表的文章便是當時研究的產物。記得結項之前,我把草稿發給沈老師審閱🫄,他和我商定好時間見面討論𓀖。我到了他辦公室坐下後,他一邊稱贊我寫得頗具模樣,一邊遞來他提前打印好的草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批註⚆,大到章節的結構性調整🤘👩🏻💼,小到標點、大小寫🔯、概念與人名的譯法。他笑著對我說,我修改好文章之後,如有意向,他樂意幫忙聯系出版🧤。現在👨🔬,每每想到沈老師我的幫助,我總不免赧顏;當時發表的文章,日後再讀之時,總感覺不盡人意🤸🏻♀️,文辭含混,論證脫節💇🏽♂️,字裏行間寫滿了別扭,無非是篇青澀的年少之作。可是🙅🏼♀️,與其說這篇文章有多少學術上的創見,還不如說,它讓我明白自己尚有一些同時寫作哲學與藝術的本事。後來我在瓦爾堡念碩士時,老師常表揚我“跨學科”的思想角度與學術能力💪🏽,我想這大概源於我在復旦的經歷吧🏇🏼。
Quention 4、在復旦,觀宇你初步接觸了西方藝術哲學的研究範式。不過🏍,國內關於西方藝術原作的資源其實並不很多🧍♂️,你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彼時在復旦的我熱愛藝術,對藝術的認識卻大都來自書本和畫冊,沒見識過幾幅名畫的原作。能在上海欣賞到的西方作品大都是當代藝術。我常舉哲學的大纛,為各處展覽大吹法螺,卻不顧自己對當代藝術也只是一知半解。可以說,我是在來了英國之後🧑🏫,才真正對西方藝術史有所覺悟🐛。

2021年春🐹,陸觀宇於倫敦攝政公園
我始終惦記著2018年夏天在國王意昂3學古希臘語時倫敦明媚動人的模樣。天氣好到不真實💁🏿♂️,風涼、無雨、日日是晴天,太陽到八九點才落山。明明我只逗留一個月,卻誤以為在倫敦已度過了永恒——我生活的新開端。國王意昂3的隔壁是考陶德美術館(The Courtauld Gallery),藏有梵高的畫像🤴、馬奈的《吧女》、塞尚的《牌戲》,學生免票參觀,於是我常在塞尚的《聖維克多山》前度過希臘文的課間。泰晤士河對岸的泰特現代藝術館(Tate Modern)也在步行距離內,當時正舉行畢加索的特展,我有幸一睹《夢》的原作☣️🙂↕️。可我最難以忘懷的,卻是初訪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觀摩歐洲早期現代藝術真跡的感覺🧑🏻⚖️。一進展廳,琳琅滿目的畫作映入眼簾👐🏼,朦朧地印刷在記憶中的名作🥴🚭,此刻竟赤裸裸又活生生地呈現在我的面前,被龜裂而黯淡的畫框襯托得無比清晰🔝、無比明亮、無比真實🧙🏻。我心心念念的畫呵!我從未和它們有過這麽近的距離。魯本斯恣肆🐈⬛、範艾克冷峻、提香陸離斑駁🔆、波提切利工巧靈動,最得我意的竟是我之前未曾聽聞的翡冷翠大畫家布倫齊諾(Agnolo Bronzino)🧑🏽🔬,端莊雅致的表象之下湧著神秘的暗流🚏。

範艾克 阿爾諾菲尼的婚禮 來源於英國國家美術館

魯本斯 洗劫薩賓婦女 來源於英國國家美術館
 提香 凡德拉明家族 來源於英國國家美術館
提香 凡德拉明家族 來源於英國國家美術館
對這些藝術品的切身體驗激發了我了解那個時代的欲望🧑🧑🧒。2018年秋✅,我開始在伯明翰大學就讀🧖,哲學系的課業比起復旦要輕松不少,我也常流連於圖書館的藝術部與歷史部👩🏼✈️。恰好伯明翰大學另有巴伯美術意昂3(Barber Institute of Fine Arts)😀,其館藏水準以於國家美術館持平而著稱🎖,上至波提切利、貝裏尼🚶🏻♀️,下至德加🧔🏿♀️、莫奈,均有幾幅作品,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與倫敦相隔兩小時火車的日子,這個與家距離二十分鐘的寶地便成了我的慰藉。久而久之,我也結識了在美術意昂3裏負責策劃活動的朋友,她知道我對藝術有些了解,於是邀請我在一場“夜訪美術館”的活動上講畫👉🏿。我在復旦時受過萬江波老師的英語公眾演說訓練,有些口才,也不太怯場,便應允下來🕵️♀️,選了挪威浪漫派畫家達爾(Johan Christian Dahl)的《母子歸船圖》,作為活動上唯一一個主講的學生,竟也收獲了不錯反響。她便再次邀請我🤞🏼,我選的是文藝復興時期畫家葛塞特(Jan Gossaert)的一幅人物畫,畫中是希臘神話英雄赫克力士與其妻迪娥霓拉。演講亦頗受歡迎🤸🏿♀️。

葛塞特 Hercules and Deianira 來源於WIKI
Quention 5、能夠感受到,觀宇你在和這些藝術品親密接觸後,更加堅定了要從事藝術史方面的學術實踐。那麽最後為什麽選擇了去瓦爾堡進行你的文藝復興史研究呢?
在伯明翰的學習讓我意識到自己的學術能力還算差強人意📠,也更加讓我明確投身學術的誌向;也正是在伯明翰👨🏿🦰,我頓悟自己對哲學🏊🏽♀️、語言、藝術史和古典學的興趣,都能糅雜在文藝復興這一時代內——古典遺產“死而復生”、哲學與藝術方興未艾、拉丁文學與白話文學(法語文學🙋🏿♀️、意大利語文學等)齊頭並進。在這裏除了哲學課外📭,宗教學系還開設了一門自擬課題的研究課,我寫了一篇論布倫齊諾的殉道者畫與基督教禮的文章🗄,算是為了自己“轉行”而積累經驗。

2020年夏⛈,陸觀宇於伯明翰
2019年👨🏻🚒,適逢復旦—巴黎高師合作項目在巴黎舉行研討會。我本身翻譯過幾篇文章的摘要🚴🏼,又想著英法兩國只有一道海峽之隔,又能見到復旦的老師們,便決定動身去巴黎旁聽⚜️。在巴黎,再次見到謝晶老師,會議結束🥬,我們和其余幾位老師在高師附近的一家酒館休息聊天。她同我說,我現在在歐洲,有機會要多四處遊歷;又打趣地向我建議道:“只是意大利要最後去,因為去了之後,其余各國自會黯然失色。”我正好和她說起自己做文藝復興研究的打算,她聽了以後非常高興,說國內研究歐洲早期現代思想史的學者屈指可數🧑⚖️🖤,做藝術史的學者也不多,因此對我大加勉勵🤟🏽。而我呢🆒🏄🏿♀️,果真“聽話”地把意大利留到了最後……
說回正題:大四時我異常懷念倫敦的文化氛圍,想著無論如何研究生都要到倫敦讀。倫敦有兩所藝術院校在文藝復興研究見長,在世界範圍內也是該領域的重鎮,其一是考陶德📆,其一是瓦爾堡。我在兩所學校都上過課,後來也被兩所學校錄取。考慮再三,我更加傾向於瓦爾堡,因為它的格局與我的專長相符,和我一樣,都不願拘泥於特定的學科😂;而它的碩士尤重語言素質的培養📼,在英國的諸多類似項目內是絕無僅有的🤶🏻☑️。

2020年秋,陸觀宇在倫敦泰晤士河畔
我忽然回想到,我的藝術之路上其實處處潛藏著瓦爾堡的影子。高中在法語聯盟讀了藝術史課後,西方藝術史的發展脈絡與各派巨擘我雖能認得一些,有名的西方藝術史家卻只知道寫下《藝術的故事》的貢布裏希🧼🤽🏽♀️。大一時,我去北京參加央視法語大賽⚰️,順道去法國文化中心探望之前詩歌翻譯大賽的籌辦人高莉🥓🖕🏽,我們在賽後還保持著聯系👇🏿。她聽說我現在在念哲學,又對藝術感興趣🪴,於是給我撕下一張便條👩🏿🦲,記下“Aby Warburg”(阿比·瓦爾堡)和“Georges Didi-Huberman”(喬治·迪迪–於貝爾曼)兩個名字🧪,讓我得閑時讀讀他們的作品。我把這張便條帶回復旦,貼在寢室的書架上🧑🏻💼,可轉念一想,法語書籍難得且昂貴🤦♀️,找書的念頭也就這麽擱置下來🔓。之後,我和謝晶老師聊起這件事🤪,她說若是我喜歡藝術,不妨從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研究》和《哥特建築與經院哲學》讀起,即使找不到原版的書籍,國內也有譯本。我唯唯,卻因學業繁冗,再次把這事拋諸腦後,只是這些名字我一直惦記著🦵🏽。大二時選修沈語冰老師的《西方現代藝術》,課後和老師談到潘諾夫斯基時,我才恍然大悟——這些藝術史家竟然出自同一宗派🤞🏿!瓦爾堡堪稱“圖像學”的開山鼻祖,潘諾夫斯基繼承的正是他的衣缽🔋。之後便是貢布裏希📂,學術上受瓦爾堡影響之外🧫,也在前身為瓦爾堡私人圖書館的瓦爾堡研究院(The Warburg Institute)任教三十余年。法國當代藝術理論家迪迪–於貝爾曼,同樣熱衷於瓦爾堡的理論,近年來在學界重新燃起對瓦爾堡的熱情🏄🏻。在復旦埋下的種種伏筆,當即讓我做出確定,在2020年秋季赴倫敦瓦爾堡研究院攻讀“文化、思想與視覺史”項目🧑🏻🏭。
Quention 6💻、能和大家詳細分享一下你在瓦爾堡的學習歷程嗎?
英格蘭的全日製碩士項目大都為一年🚟。在瓦爾堡的一年🧜,雖因疫情與封城而備受煎熬👨🏿⚖️、幾近崩潰,現在回想起來卻總有如魚得水之感。極具傳奇色彩的圖書館暫且不論,課程設置本身便頗合我意——除無考核要求的學術方法課外👴🏿☠️,碩士生有兩門必選課,一門講早期現代歐洲思想史,一門講文藝復興藝術史⚃,皆是我喜歡的;另有兩門選修課,我選了一門建築史和另一門書本史(History of the Book),在歷史的不同分支之間融會貫通🤶🏿。再者就是語言和古文字學的學習。碩士生一人要修兩門語言,我選的是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也同時修讀了這兩門語言的古文字學(palaeography,即研究字體流變之學問,熟識後方便辨讀抄本與古書)🏊🏽。開課之前的分班翻譯測驗,拉丁文我還算得心應手,意大利文我本一字不識,將其權當法文👷,也能懂個大概👨🏻🦲,後來稀裏糊塗地分到了高級班。瓦爾堡的語言訓練強度可觀🐛,尤重閱讀理解與翻譯🏨,不管聽說,兩個學期的課程都以翻譯十四至十六世紀的史料為主🙆🏻♚。我咬牙堅持🤷🏽,到第二學期竟開了竅,雖然口語表達仍似牙牙學語的孩童,只曉得面包🎧、水與玫瑰,可是如需閱讀意大利文寫的材料👋🏻,有字典傍身🤷🏽♂️,亦能應對自如。我想在之後牛津讀一個現代語言的學位🤲🏽,就是希望自己能夠在研習早期現代意大利文學與思想流變的同時🤾🏽♂️,提升自己聽說讀寫的語言水平👊🏿。
在瓦爾堡訓練了兩學期後🧑🏿⚖️,我見自己意文功底漸長,畢業論文也選擇了一個較有難度的文本——1499年於威尼斯印製的《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一書(標題直譯蓋為“普麗斐羅的睡夢-愛欲-戰鬥”,我還沒想到合適的中文譯法)。該書誕生於歐洲書籍的“繈褓之年”(the incunabula period,約為1450至1500年),語言矯揉造作👩🏻🏫,混雜意大利白話與拉丁文,亦從維特魯威與阿爾貝蒂處沿襲建築領域的專有詞匯🏋🏻♂️,卻因為其精美絕倫的171幅木板插畫,尤首一眾藝術史家的賞識。我的論文便討論其文字與圖像間的關系,論證這部向來被視作自成一派的作品,其實受十五世紀晚期意大利兩種傳統的影響🌭,一為插畫書本,一為修辭論著。兩派作者都欲將書本的內容“投於(讀者)眼下”(拉丁短語“oculis subicere”均見於兩派文本內),只是采用了圖像與文字這兩種不同的策略罷了。我是頭一次著手兩萬詞的長文🫷🏼,寫作時不免推倒重寫♔、空勞神思🧝🏼♂️,本不充裕的時間更是捉襟見肘🦈。所幸我的導師舍曼教授——也是瓦爾堡研究院的現任院長——是書本史領域的泰鬥;受其指點🧒🏼,文章最終才算瑕不掩瑜🦃,取得不錯的成績。論文剛提交後,我寫郵件給導師致謝👱🏼,他片刻後即回信,打趣地說自己“由衷地感謝天上的神明⏺,縱使在去年向人世間投下了種種困厄🧝🏽♀️,卻把你引到了瓦爾堡來”。郵件末了,老師的語氣認真起來:“這裏永遠是你的家。”
 2021年冬,陸觀宇於倫敦瓦爾堡研究院
2021年冬,陸觀宇於倫敦瓦爾堡研究院
Quention 7、從你的介紹中能夠隱約感受到,你在瓦爾堡的學術生活其實和哲學話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研究本身又和哲學學科有著界線。
決定投身文藝復興,並不意味著與哲學訣別。不管我之後研究怎樣的時代、文化、人物👨🏽🏫、作品,只要其反映出某種思想特質🔳,只要我審視以理論與批判的眼光,那麽我想我與哲學將始終保持著密切關聯🎣。撇開學術不談🧑🚒,本科四年的哲學訓練也陶冶出了我現在為人處世的諸多準則——獨立🐬、開放、冷靜,包容差異、尊重人性等等。在分歧甚囂塵上的世界,是哲學給予我信念去尋找共識,去在共識上厘清我與他人立場的預設、追溯分歧的源頭。這些特質或許是愛好人文的學子所共有的🍪;對思辨的熱愛🕘、對人性的執著✉️,讓我們有能力穿透激情與修辭的迷霧♚,努力彌合我們社會中盈滿血汗的一道道裂痕。
而且,除了塑造我的人格與社會責任感™️,哲學也讓我反思我與學術之間的關系😦。大二時的《現代英美哲學》課堂🍳,孫寧老師曾說🗿,哲學無非哲學家各自的世界觀,我深以為然。轉念一想✒️,學術或許亦如此🐘。浩瀚而雜亂的知識,只有在納入屬於自己的體系之後,才能化作個人的思想與智慧🛄。因此🤟🏿,哲學也好🛄、歷史也罷🐊,治學或許正是作為自我的主體去理解、去闡釋、去接近作為哲學“真理”或歷史事實的客體之過程;學術首先是屬於自己的事業。
Quention 8、我想我們對這五年長途的最後一個問題或許可以問的大一些——是什麽讓你始終保有對哲學和藝術生活的勇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感受到你身上的這份熱情的勇氣🎅🏿。
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我的本科畢業論文入手來解答。我的畢業論文以法國女性主義哲學家波伏瓦為題。這個選題,或許源自我對法國哲學的興趣🏃🏻♀️👉🏽,或許源自我對女性主義的興趣;可是從我的個人經歷來看,我選擇波伏瓦🛀🏻,或許是因為在伯明翰的兩年👨🏻🦽➡️,我開始遭遇自己生活與身份上的危機。危機的一部分原因正是在於🤝,我意識到在自己追求的學術道路中🐤,我的“主體性”總會突兀而尷尬地橫亙在那裏——我的治學方向,歐洲的文化🫎、歐洲的理論👰♀️、歐洲的語言👩🏿🦱;而我🧗🏻♀️,中國人🫷🏿、亞裔、非母語者⚙️。我意識到在未來幾年內,自己的學習、思辨與寫作或許都將以英文為主,而不管自己多麽能用英文侃侃而談,一個不倫不類的措辭、一個不由自主的語病、一個不合時宜的重音,都能讓自己在同儕面前瞬間“原形畢露”,在說歐洲語言的學界做一名狼狽的來客。
當我為此困苦不已之時,卻在波伏瓦的《第二性》中找到了慰藉。我在大一時曾囫圇讀過這本書,當時直接跳過引言🔡,在主講生物的首章中昏昏沉沉;時隔三年再讀這本書🧓,我卻忽然留意到,引言中寫了這樣一則軼事👘:
“有時候,在討論抽象話題時🤹🏿,我會感覺厭煩🧑🏻🏫,因為聽見男人告訴我:‘您這麽想🧋,是因為您是女人’;可我知道我唯一的辯護只是這麽回答🎄:‘我這麽想📌,因為這是真的’😸,從而消除我的主體性。我不太可能頂嘴說🦝:‘您的意見相反,因為您是男人’,因為已經默認了身為男人的事實沒有什麽特殊的。”
要麽把性別排除在自己的主體性之外,要麽屈服於對女性的刻板印象🧲:波伏瓦所面臨的抉擇讓她意識到,在當時學界的氛圍中👳🏿♂️,自己的位置只能是特殊的。然而🧑🏽,這卻啟發她思考——從她自己的個人境遇出發,思考全體女性在社會中共同面臨的壓迫與處境,思考她們作為女性而探討“抽象話題”🍱、從事哲學工作的可能性與方式。《第二性》便是波伏瓦作為女性的主體性之產物👰♂️。正是這樣一部作品🦬,讓我堅毅起來,讓我逐漸認識自己中國學者的身份對自己👩🏼✈️、對學界的意義🧘🏻♀️。我酣暢淋漓地寫完畢業論文——那是在2020年的春天,疫情初步放緩🧗🏿,伯明翰春意盎然🚱。文末,我意猶未盡地續了幾段文字作為後記。我寫道💐:
“閱讀波伏瓦使我勇敢。她讓我直面我自己的主體性,正如她直面她自己的主體性一般。她並沒有逃避自己身為女性的事實,卻轉而思考,女性和男性——她和他的男性對話者——如何同時作為自由的主體接近客觀的知識👀、了解普遍的真理🛼。波伏瓦或許並未意識到自己有多勇敢🦻🏼🧑🏽🚀。她將自己的學術成就歸功於薩特♣︎,在哲學史上也屈居薩特與梅洛-龐蒂的陪襯。可她不自知的勇敢卻感染了許多人——許多女性主義學者、許多女性學者🍓、許多女性🤾🏿♂️,她們意識到,自己也本應該是自由的主體,因此也本應該可以自由地進行學術思辨,平等地與他人談論抽象話題🪝。更重要的是🎥,在接觸那些被奉為客觀的、絕對的、經典的知識時,她們意識到,她們不應該取消自己的主體性🔉,而是作為女性去駕馭這些知識。”
於我而言,波伏瓦的意義亦如此。她為我本科四年的哲學生涯畫下句點,卻賦予我勇氣與意誌,讓我以中國學者的身份探索歐洲的——以至全人類的——文化成就與歷史脈絡,消弭心中因為自己的主體性而產生的隔閡👷🏿♀️。來到瓦爾堡之後,原先的這種尷尬反倒化作我對學術之路的堅定;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與我的同儕平等交流、彼此啟發👵🏿,同時秉承著對中國學界、中國文化與中國社會的關切🏊🏼♂️。我對翻譯的誌向也讓我對中國的文字保有一種使命般的親近。
這是波伏瓦帶給我的🥎,或許也正是哲學帶給我的🤦🏿♀️。我想,在自己未來人生的重要關口,哲學或許會繼續伴隨我,幫助我作下決斷🌡🧼,賦予我前行的力量♉️。當我為了自己的人生軌跡而苦思冥想之時✪,我時常想起在哲院聽紐約州立大學的趙穗康教授講學之時♾,他同我說的話🎫:“將來你會發現👨🏼🔧,你曾經熱愛過的,都會再回來🏖。”我熱愛的哲學,是我生命的一段主題旋律。
Quention 9、觀宇💆🏽♀️🦍,謝謝你🚵🏽♀️。你敞開自己的心扉和我們分享這五年來相遇的人🫳🏿、事、物,回顧一段五年的長途不是一件那麽容易的事情👩🏼🌾🏂🏻。再次感謝!
也非常感謝你,沁雨,給我這次受訪的機會👼🏽。於我而言,反思這五年的“學途”,讓我探明我過往的線索,讓我與之前的自己言和,讓我看見復旦與哲學在我靈魂上深深的烙印。
可我更加希望這場訪談能為與我同道的朋友們帶來些功用:在他們在因與我類似的遭遇而困頓不已的時候🧖🏽,我希望我的生活點滴能為他們帶來些許寬慰與啟迪🐣👨🏻🦼。感謝願意傾聽的你🎨,感謝願意傾聽的你們👩🏿🔬,我期待在下一個五年之後,再與你們分享我的故事。
編者手記👨🔬:本期,新晉羅德學者陸觀宇同我們分享了他這五年之中由哲學轉向文藝復興研究的心路歷程以及關於勇氣的真誠回答🧑🏼💻。
正如觀宇最後所引的一句話:“將來你會發現💅,你曾經熱愛過的,都會再回來♝。”讓我們都揣著一個赤誠的心、懷著一些無畏的勇氣🚨🧜🏼♂️,堅定地走在我們各自的道路上吧。祝福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