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宋·宋代之儒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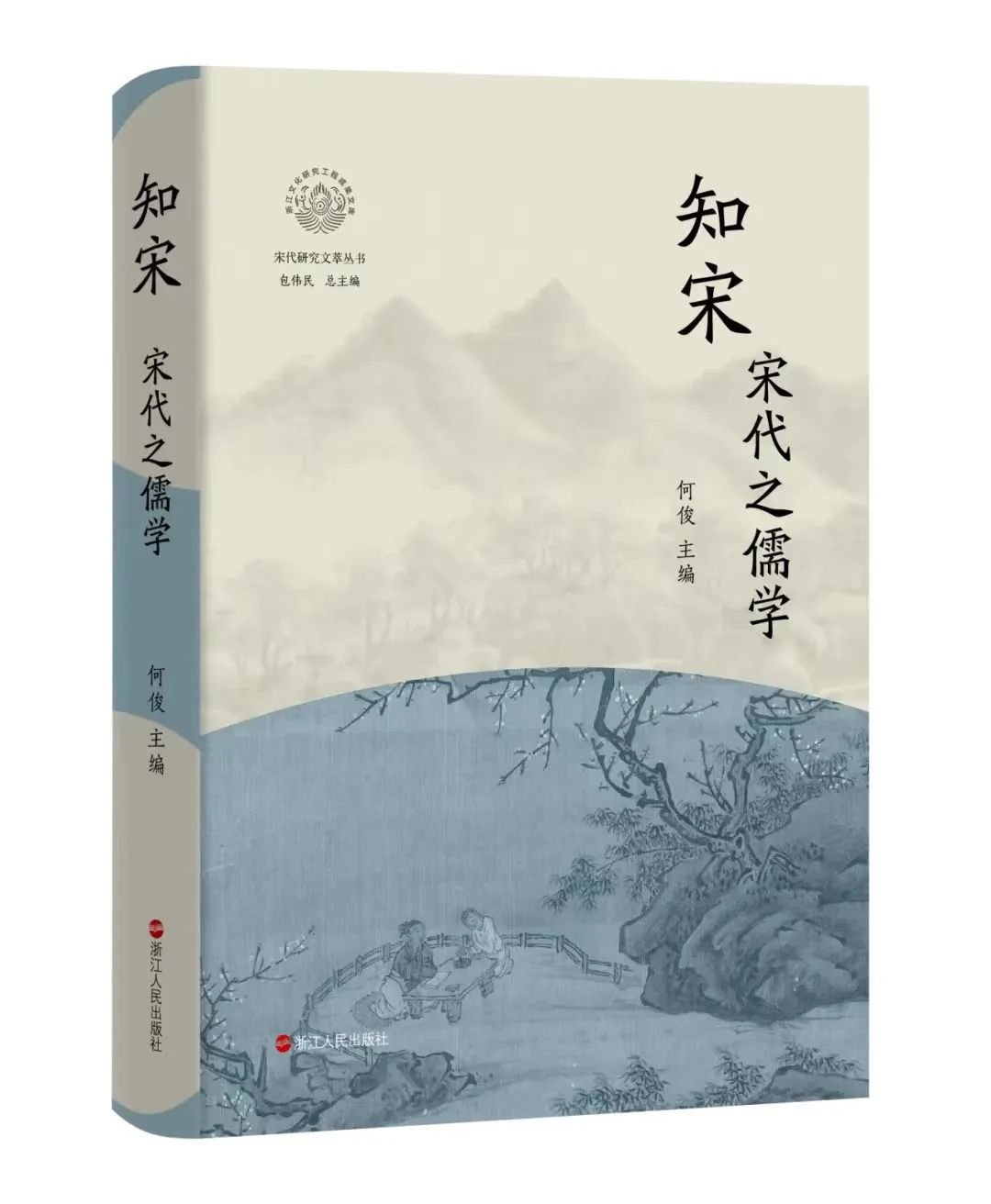
主編📥:何俊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月🥴:2023年11月
《知宋·宋代之儒學》重點關註宋代儒學的發展🧑🏻🚀,分上👩👦、下兩編。上編依年齒選鄧廣銘、徐規、陳植鍔先生與陳來👨🏽🎨、王瑞來教授共七篇文章🧎🏻♀️➡️。下編收入編者何俊教授近年分析宋學初興時胡瑗湖學與宋學完型時朱子理學、象山心學🎠、水心事功學等四篇文章。上、下兩編互補,引導讀者對宋代儒學獲得一個兼具宏觀與微觀的認知。
起初,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同誌示知有《知宋叢書》的出版計劃📨,由包偉民教授主持🌍👩🏿🎓,其中《知宋:宋學》一冊囑我選編,後定名《知宋:宋代的儒學》。“宋學”與“宋代的儒學”是不相同卻易混用的指稱。宋學是傳統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一種範式,與漢學相對🏄🏽♂️,宋代的儒學則是一個斷代的概念。由於宋學完型於宋代,宋代的儒學是宋學的典型,因此常常用“宋學”來簡稱“宋代的儒學”💇🏼♀️✂️。今書名定為《知宋🏄♀️:宋代的儒學》,限定於斷代,但因所收論文涉及“宋學”概念的使用🥚,特作說明。
是編原定目標是通過這一文集窺知百年宋學研究的全貌,但經過文獻調查,三思而確認自己既無此能力,亦無此興趣🦸🏻♀️。無能力,蓋因百年來正是現代中國學術全面取代傳統中國學術的歷史階段🧙🏼,無論是對於宋代的儒學🧓🏻😰,還是宋學,研究成果汗牛充棟,海內外名家眾多,要於20余萬字的論文選編集反映這一領域的整個學術史,斷非能力所及。無興趣,則因思想與經濟、製度等史事有所不同,後者或可秉持科學的治史觀念,獲得一客觀的認知,但前者無論是對象👵🏼,還是研究,都是一主觀的認知,個人旨趣構成了難以抹去的底色,故與其借客觀之名以售主觀之實,不如據實而行🤾🏼♀️。
《知宋叢書》由包老師主編🤖。包老師是徐規教授(1920—2010)的碩士🤹,鄧廣銘教授(1907—1998)的博士,我第一次參加宋史研討會即與包老師住一起,得他照顧,《宋學:認知的對象與維度》亦是包老師當年囑我撰寫的🚨,今以之代為是編導言,良有以也🫔。整個文集的選編原則😮💨,一是海外研究一概不選,二是國內研究只選我的老師及其相關二三前輩的論著🈵,加之我自己幾篇拙稿,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依年齒,首選了鄧先生的《略說宋學》,鄧先生是我的碩士生導師之一陳植鍔教授的博士生導師🧑🏼💻。再選了徐先生的兩篇論述陳傅良與葉適的論文🖖🏿,前者發表於1947年,後者初稿於1963年,改定發表於1989年🏞,以見徐先生對故鄉之學的專註。我與陳植鍔老師都不是徐先生體製內名下的學生🫐,但我因世誼👵🏻,陳老師因鄉誼,都是徐先生的門生👩🦱。徐先生不僅是引我進入學術的啟蒙老師🧰,而且在宋學研究中具體指導我從永嘉學派入手,並帶我參加宋史年會🆔,引我加入宋史學會。徐先生是王禹偁專家,著有《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陳老師的論文《試論王禹偁與宋初詩風》(《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便是在徐師的指導下寫成的🕵🏻,陳老師的博士論文《北宋文化史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的清樣亦是請徐師審校全稿的。然後是選了陳植鍔老師通論宋學及其精神的兩篇論文🔷。三位前輩老師關於宋學的論著頗多,因已故,故所選全是我的主觀🧔🏼。最後是陳來教授與王瑞來教授各一篇☞,他們分別是陳植鍔老師的博士生學長🤑、本科生同學🤳🏻,與陳老師既為學侶,又多年指點與幫助我,只是他倆都是著述弘富👨👩👧👦,我實不知如何選,故請他們自薦一篇。陳來教授選了他的代表作《朱熹哲學研究》中專論朱子與李延平在一章,真是甚合是編專重師承之意🦴。王瑞來教授選了討論江南儒學的新作,則是對我近年工作支持的表征。在此一並謝過。如果上編是師說部分👨🏽🦳,那麽下編可謂是續貂部分,收入了我最近幾年分析宋學初興時的胡瑗湖學與宋學完型時的朱子理學♌️、象山心學🤸♂️、水心事功學的四篇拙稿🙌🏼。
雖然是編純為一主觀性的選編文集,但我仍然希望能引導讀者對宋代儒學獲得一個兼具宏觀與微觀的認知。若能進一步引導讀者進入宋代儒學,體會到宋代儒學“學統四起”的精神自覺🦟🧑🦱,並進而認同這樣的精神自覺正是古今中外思想豐富多樣性的動力與保證,則幸莫大矣。
何 俊
癸卯元宵後一日於雉城
導 論
宋學💗:認知的對象與維度 ……… 何 俊 / 001
上 編
略談宋學
——附說當前國內宋史研究情況 ……… 鄧廣銘 / 011
陳傅良之寬民力說 ……… 徐 規 / 028
略論葉適的學術和事功
——紀念葉適誕生840年 ……… 徐 規 / 038
宋學通論 ……… 陳植鍔 / 050
論宋學精神 ……… 陳植鍔 / 074
朱子與李延平 ……… 陳 來 / 102
宋元變革視域下的江南儒學 ……… 王瑞來 / 129
下 編
權力世界中的思想盛衰悖論
——以湖學為例 ……… 何 俊 / 161
程朱理學的話語型塑
——以《論孟精義》為中心 ……… 何 俊 / 179
本心與實學
——兼論象山對心學譜系的疏證 ……… 何 俊 / 232
葉適事功學的自我疏證
——《習學記言序目》劄記 ……… 何 俊 / 257
後 記 ………何 俊 / 306
宋學:認知的對象與維度
何 俊
由於“中國所以成於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因而宋代的思想文化曾不幸地成為追求富強的現代中國在文化上強烈要切割的東西;雖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有過理性的認識,但至中葉仍遭到徹底革命👨🏿🦳。然而否極泰來,“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1980年,宋明理學研討會在杭州召開,催破了長期以來認為宋明理學是封建遺毒的思想自蔽症,從而啟動了中國大陸在新的歷史時期對於宋代思想文化的重新認識與理解💻,並很快在整體認識🐦🔥、個案研究以及文獻整理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與此同時,港臺地區與海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也逐漸進入大陸學界,人們發現🧑🏿🦱,在此領域中的研究,20世紀中葉的港臺地區與海外接續著三四十年代,不僅沒有中斷,而且成果甚豐。
遭到徹底革命的主要對象是以朱陸為代表的宋代道學👵🏽,這在現代中國已完全西學化了的學術建製中👨👩👧👦,歸屬於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故而復振中的宋代思想文化研究直接呈現為中國哲學中的宋明理學研究,歷史學中的中國思想史的相關研究亦有涉及✢。至於在宋代哲學與思想的解讀模式與分析方法上,20世紀80年代剛剛擺脫蒙昧的大陸學者仍然局限於單一的唯物—唯心與階級分析👮🏻♀️。不過,這樣的解讀模式與分析方法最大的問題也許並不在其本身,因為後來不斷花樣翻新的解讀模式與分析方法雖然可能更顯得合理👉🏼,但是從本質上講,同樣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外在“格義”與思想文化的“科學化”傾向。唯物—唯心與階級分析的真正弊病在於它的單一性,以及它挾持著官方意識形態而彰顯出來的僵化壟斷性。
當大陸學者在解讀模式與分析方法逐漸擺脫單一僵化的唯物—唯心與階級分析以後,宋代哲學與思想呈現出了自有的豐富與深刻,但是相應的問題也不期而至。原來在唯物—唯心模式梳理下的宋代思想研究,學者們為了形成所謂的哲學黨性,必須將視野延拓到朱陸兩系以外的思想者,比如這時期的代表性著作侯外廬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但在解讀模式與分析方法的壟斷解除以後,多元性的方法被專施於以朱陸兩系為代表的思想者,結果方法上的多元性在某種程度上與內容上的局限性形成了一種反襯🔆。這種現象的造成,固然有來自港臺與海外學界的影響,但不能否認更多的是來自中國傳統儒學史觀中的道統意識的束縛🈸🤵🏽。此外🪮,階級分析法的擱置♧🦋,加之學科間的隔閡,使得宋代哲學與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從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抽離出來🪔🍴,呈現為抽象的哲學觀念的演繹。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後期🏌🏽♀️,研究開始有所突破🤾。其一,宋代哲學與思想並不能局限於以朱陸兩系為代表的理學,鄧廣銘的論文《略談宋學》通過標示傳統的“宋學”概念強調了這一意見。賦予了新內涵的“宋學”概念雖然遠沒有經過嚴格的界定🤹🏽,但其基本意圖是非常明確的,它強調的是更廣論域中的宋代思想文化。其二➜✣,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新典範的出現🧑🏻🚀🫅,由大陸出版的余英時的論集《士與中國文化》雖然不是專門研究宋代,但對宋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卻有著同樣的示範意義🍺。這一示範作用在學術上的具體引領無疑因人而異,然而有一點是至為明顯的,那就是在歷史學註重分析—綜合這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上🧏♂️🤼♀️,如何擁有並貫徹問題意識。其三🚕,唯物—唯心模式與階級分析方法的壟斷性此時遭到更徹底的解除,新觀念與新方法被引來審視宋代的思想文化👷♀️。前文論及這一現象時🩻,或著意指出隨之而來的問題🙎🏼,但其前提仍是充分肯定新觀念與新方法審視下的宋代思想文化呈現出了它的豐富與深刻,毫無疑問,這樣的前提是基本的🕚、主要的🧑🏿🦲🦆。
上述三者👨👩👧👦👩🏻⚖️,都有交疊的層面🤛🏼,但側重也明顯。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將其一歸為內容,後二者歸為方法👐🏽,以此來討論🐲。
在《略談宋學》中🙍🏼♂️,鄧廣銘有著否定理學為宋學主流的隱意識7️⃣,約20年後漆俠在《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中力挺荊公新學是將這種隱意識完全顯性化了。但鄧廣銘文章的基調仍在強調宋學的廣闊性,這在陳植鍔的《北宋文化史述論》中得到了充分具體的展開。它突破了道統的窠臼👨🏿🔧,對北宋思想文化進行了縱橫交織的梳理💇🏻♂️🧎🏻♂️,至今仍堪稱此一領域的重要論著。概言之🙎🏽♂️,此後關於宋學的研究,雖然對於誰為宋學主流各有見解,但宋學決不限於理學🛥,無論在意識上🦶✍️,還是在具體的研究中,應該是無歧義的。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關於宋學的上述理解在內容上是不可質疑的👨🏻🦰。眾所周知,宋學是清儒為了確立自己的學術定位及其正當性而提出的一個學術史概念。依照這個概念,宋學是一種學術範式,濫觴於中晚唐👩🏼⚖️,完形於兩宋,橫肆於元明💢,斷非一代之學術。事實上🧚🏽♀️,經歷了“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鹹以降之學新”三個階段的清代學術,在“國初”與“道鹹以降”兩個時段中,宋學仍然構成重要的內容⏪。甚至可以說,整個20世紀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也是基於宋學的精神而脫胎於宋學的🌎。因此非常清楚,前述關於宋學的理解,根本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基於斷代史研究的述說🔢,它充其量只是突破了理學的籬笆,標示了理學以外各學派的存在,而完全沒有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種跨朝代的範式意義上的考慮🚑。
進而言之😙,如果我們承認,宋學在兩宋的完型最終呈現為理學,而理學從南宋後期開始一直到近代中國,不僅作為一種學術範式而存在🚴🏻,更是作為一種近世中國的文化形態而存在,那麽前述對宋學的理解更為局限🤜✥。因為當理學由學術轉型為文化以後,以宋學這一新的學術範式所展現出來的新儒學🪑,實際上根本已非思想學術層面上的宋學概念所能籠罩🙇♂️。或者,如果我們沿用宋學這個語詞,那麽它的內涵應該由學術範式擴展為文化形態。最新的研究其實已經表現出這樣的企圖,包弼德在他的《歷史中的新儒學》中就試圖將完型於兩宋的新儒學放置在時間上從晚唐到明代🪟,內容上從觀念到社會的範圍內加以分析。
至此,我們可以對作為認知對象的宋學在性質與內容上嘗試著有所界定🧿,認為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史的一種範式,並最終衍生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一種文化形態,它濫觴於中晚唐,完形於兩宋,橫肆於元明,嬗變於清代🌮,而且構成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與文化的基礎👨🏿🎓🏊🏽♂️。但是,我們隨即產生這樣的問題:從一個傳統的術語,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考釋,變成如此寬泛的一個概念,一個甚至是不嚴格的術語,是否有必要沿用在現代中國學術的研究中呢🫷🏽📕?比如剛剛提到的“新儒學”(Neo⁃Confucianism)這個術語,在一般意義上似乎就可以取代“宋學”,它在西方學術界一直使用,在中文學術界也已被接受👷🏿♂️,盡管它在內涵上的不清楚可能更有甚於宋學,包弼德的新書其實也折射出了“新儒學”一詞界定上的寬泛性與不確定性🦝。
我們似乎也可以由實際的研究來進一步佐證“宋學”作為一個現代學術術語的無關緊要性。前文言及,宋學在新時期的重新研究最初主要在中國哲學的領域中🫲🏿。由於學科的專門性👅,限於斷代史的宋學界定沒有成為中國哲學關於宋明理學研究的某種負擔,學者們通常將宋明理學作為完整的對象加以討論🧵。但是,在這樣的研究中🙋🏽♂️🏂🏻,宋學的觀念同時也是一個缺席的觀念🙋🏿♀️,它幾乎沒有起到解釋框架的作用,關於宋學作為中國傳統學術的範式的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當淡化的。以陳來的研究為例略加說明🧑🏼⚕️。從《朱熹哲學研究》開始,中經《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到《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在陳來20年的研究中,分涉整個宋學發展過程中最重要階段的最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其解讀基本上是透過西方的哲學框架進行的,從早期的本體論👩🏻🦽、認識論,到後來的存在論🤨、詮釋論🤹🏻♀️,傳統的宋學觀念並沒有成為分析考慮的維度,而重要的是👨🏿⚖️👨🦽➡️,這並不影響他以心知其意的態度來理解古人的哲學建構。
的確🧑🏽,就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的整體性西學化轉型而言,襲用並延拓宋學這樣的傳統學術術語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如果說建構現代中國學術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知識——就歷史學而言,則是為了獲得對歷史的認識與理解——那麽傳統的術語實際上又是無法繞開的🥫,因為正是在宋學這樣的傳統術語中保留著歷史的信息⤴️,尤其是為了理解歷史文化傳統的獨特性🧑🏽🏭。不唯如此,建構“現代的”中國學術即便是既不可避免,又理所應當呈以整體性的西學化轉型,但承續與更化傳統中國學術仍然是其中應有之義,而且是現代“中國的”學術真正得以確立的重要條件,因為普遍性(現代的)固然是學術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但獨特性(中國的)卻是學術獲得意義的根本🧙。這就意味著,無論是就歷史的認知,還是就歷史學的建構,宋學這樣的傳統學術觀念既構成認知的對象👨🏼🍼👱🏽,同時又成為認知的工具🧗🏻♀️。就認知的對象而言,即上述宋學所涵蓋的內容👔;就認知的工具而言,便涉及所謂的方法。
以促成宋學完型的理學而論,當研究者以西方思想的架構來解讀時,不僅理學的言說方式及其意蘊,比如解經釋史,不可避免地遭到忽視,而且理學的結構與脈絡也將被消解👩🏻🦯➡️💃🏼。即便在文本的意義上也是如此🕤,比如完整表達理學架構的《近思錄》,其體系便很難受到理學研究者的完整對待。相反,如果研究者能夠保留傳統宋學的維度🧑🏿🍼🍻,那麽整個的解讀將會沿著更貼近歷史對象的方式展開🧪。換言之,當宋學作為一種認知維度引入時🧔🏻♂️,它實際上能夠為認知歷史本身打開有益而重要的視域👨🏿🎓。
如此說,並不足以反證西學語境下的宋學透視是不可取的,而只是欲以表明當以西學的架構來透視作為認知對象的宋學時,如何兼顧來自傳統學術的認知維度😢。這樣的學理,其實無甚高論🌋,但是真正要成為研究中的自覺意識,卻也並不容易🔽,至於落到實際的研究中而能嫻熟運用✅👨🏼🚒,則更顯困難👟。唯此,前文才述及余英時的著作最初在大陸出版時在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典範作用🫱,如果專就宋學的領域,他晚近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無疑更屬於典範性的著作。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唐中晚期至清前中期的長時段學術思想史領域中,研究內容已拓展得很寬,研究方法也呈現出多元化🙍🏿♀️,當我們以宋學為題來討論時,一方面無意於以宋學來範圍這個廣大的研究領域,或左右研究的進路,事實上如有這樣的企圖🧚,不僅是狂妄的🫧⬇️,也是徒勞的;另一方面也無必要去羅列與點評各種研究🖖。我們真正意欲表達的是,如果我們認為,在研究中尊重某種假說,並願意以之作為研究的一種預設🐜,加以證明或證偽,都是學術獲得進步的某種有效方法。比如在唐宋以降的研究中,內藤湖南的唐宋轉型說被學者們廣引為預設👮🏿♀️,又比如哈特維爾在《中國750—1550年在人口、政治和社會的轉型》中所提出的那些論點,也已構成美國後輩學者研究的重要預設🧑🏽🎤。那麽,我們看到,清儒用來概括前代學術思想範式的宋學概念🤦🏽,經過現代學者的再引用與內涵延拓♿️,同樣應該並能夠成為我們認知的前提預設,因為它不僅為我們標示出認知的範圍🔡🤹🏽♂️,而且為我們提供了某種認知維度。
試以具體的研究加以說明🥡。宋學的研究已不泥囿於抽象的哲學分析,道學家也不再只是生活在形而上的世界裏,從註經文本到道學話語,從政治文化到社會文化,每個分支都有拓展🧙🏼♀️🙋🏽,但是這些研究極容易被分別歸屬於從經學史到哲學史©️🕹、從政治史到社會史的學科壁壘中,而難以被統攝在對作為思想範式與文化形態的宋學的真正認知上🤦🏼♀️。反過來,各有歸屬的這些研究其實也容易陷入有形無魂的困境。換言之,宋學作為一種統攝性的認知維度是有助於擺脫這種困境的。相對於這種從自身研究內容拓展而引起的宋學維度的消解,對於以精英為主的傳統思想史構成另一種巨大挑戰的👏,莫過於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雖然不能說在這一著作中🖇,葛兆光完全企圖用小傳統來顛覆大傳統❗️,但他無疑是要極力彰顯非精英思想來重構思想史。但是🤷🏼,當我們意識到🤸🏿♂️,以宋學而言🎅🏿,新的學術思想範式的形成本來就與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新的學術思想範式進而衍化為文化形態更是構成非精英思想的土壤♉️,因此,彰顯非精英的層面👨🏿⚕️⬜️,在研究上,無論是側重思想史而關註知識🌹、信仰等,還是側重社會史而關註家族👐🏿、儀式等🎉,作為思想範式與文化形態的宋學仍足以提供一種有益的認知進路和維度。
(原載《歷史研究》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