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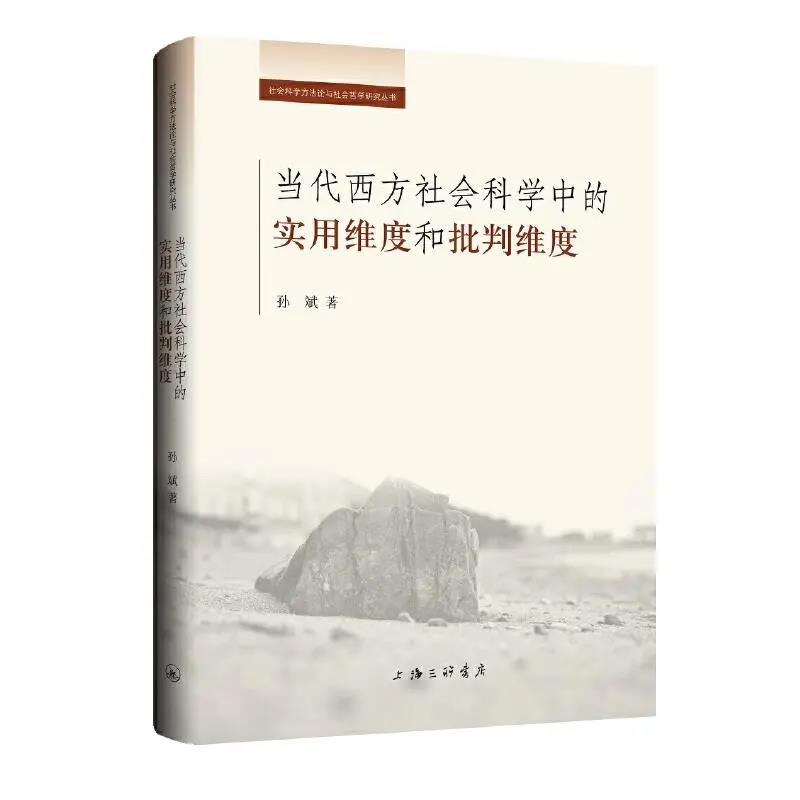
書籍信息
作者🎮:孫斌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年月:2020年10月
ISBN🌖:9787542671226
作者簡介
 孫斌,哲學博士,意昂3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藝術哲學🎅🏻、當代美學、西方哲學🧘🏻,出版專著《審美與救贖:從德國浪漫派到T·W·阿多諾》等、譯著《作為經驗的藝術》等💂🏽♂️、編著《當代哲學經典·美學卷》📔,在《文學評論》、《哲學動態》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孫斌,哲學博士,意昂3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藝術哲學🎅🏻、當代美學、西方哲學🧘🏻,出版專著《審美與救贖:從德國浪漫派到T·W·阿多諾》等、譯著《作為經驗的藝術》等💂🏽♂️、編著《當代哲學經典·美學卷》📔,在《文學評論》、《哲學動態》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目錄

前言
一直以來🈂️,我們似乎總是在我們願意和樂意承認的領域中取得成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自身日益成為一種復雜的東西,或者說,我們日益以復雜的方式來對待自身。可以爭論的是,究竟是這些成就作為外部原因使我們變得復雜🫢,還是我們的復雜通過這些成就為自身開辟了道路。但無可置疑的是,就我們乃是由著這種復雜來構建知識和采取行動而言,我們不得不把它當作一個基本的語境來考察✊。這樣的考察被歸結到社會科學的標題之下,因為就社會以公共的方式體現我們自身的諸般關系而言🔳,恐怕沒有什麽任何其他東西比它更能刻畫這個語境了。事實上,那些屬於該標題的諸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學科已經進入當前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學科行列☕️;人們把熱忱的思考貢獻給它們,並通過它們轉而貢獻給自身,仿佛恰與德爾菲神廟上那句神諭的意思相契合❕。
這些思考越是發展,就越是把一個問題追認為是前提性的,這就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眾說紛紜的觀點:社會科學有其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結構性特征,因此必須擺脫後者的影響🌃📊;社會科學是從自然科學那裏獲得其基本框架的,因此必須以前者為理論原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有著共性的東西,因此可以彼此溝通和分享,等等👨🏿🏫。不難發現🔥,這些觀點不盡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但有趣的是,它們非但沒有阻礙社會科學取得成就,反而各自發展成為有啟發性的思想進路。這恐怕只能說明社會科學或者說思想本身的活躍性,它們從來沒有被全部給出,而總是在它們的過程中成為自身,就像黑格爾說的👰🏽♀️,“這便是思想的情形,即它只能在生產自身的過程中發現自身🧝🏼♂️。” 唯是之故,邏輯上的前提可以並且往往在時間上的遲後被追認🧑🏻🎨。
社會科學理論中許多論爭特別是派別的論爭,歸根到底恐怕都與上述情形有關💤。而我們更願意從這個情形中承認一個事實,即🕵🏼♀️🤦🏿♂️,我們既用社會關系去解釋物理現象⚪️👨❤️💋👨,也用物理關系去解釋社會現象🎼。在這裏,顯而易見🎋,我們無法把何者認定為是第一位的。不過🛋,要緊的還不是這個🤚,而是解釋🤏🏻,解釋意味著我們藉著思想從直觀的狀態中擺脫了出來。即便像感覺這樣看似極其直接和私人的東西也不就是直觀,這就如同約翰·杜威(John Dewey)所說,“辭典告訴查閱它的人,像甜和苦這些詞早期的用法並不是像這樣指感覺的性質💪🏿,而是將事物辨別為贊成的和敵對的。”事實上👨🏼🎨,社會關系以及物理關系本身已經就是解釋的結果了🤹🏼♀️,當然更重要的,它們仍然處在解釋的過程之中。就此而言😷,解釋也是一種塑造🧑🏻🦯,即它塑造了事物由以於其中獲得其自身意義的關系,這樣的有意義的事物包括有意義的我們構成了我們的世界。
要說明的是✊,解釋和塑造的只是關系🎥,而不是意義🈵,意義是在關系中自行生產和呈現的。在這個尺度上👩🏼💻,即在讓意義世界自行呈現的尺度上,那些觀點和論爭並沒有實質性地彼此為敵。但是👩✈️,敵人還是存在的,這就是技術化的態度🧑🏻🔬。技術也是一種關系,因此它不生產意義,而是守護、照看和管理意義👨👩👦👦,就像它在歷史上一直所做的那樣。但是🏊🏼♂️,“這就仿佛,一個傑出的花草布置者最後會認為,他自己至少也生產了一片非常微小的草葉👩🏻🍼。” 維特根斯坦的這個比喻是意味深長的。相仿佛地🧛🏼♂️,就這裏的討論而言,我們無法追溯到可被指認的技術專家🤟🏻,即某位花草布置者,但我們可以追溯到一種技術化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意義的生產被管理冒名頂替了。冒名頂替的生產當然不是真正的生產,而是以管理之實所行的意義的挪用、拼湊和扭曲。事實上,前面提及的那些有影響力的社會科學學科正面臨著這樣的危險。
為了避免或者至少降低危險,社會科學不應該也不能夠放棄檢討的契機🥷🏽,而檢討正是社會科學理論本身構成的一部分。本書檢討為當代社會科學提供理論資源的兩種思潮:實用主義和批判理論。這兩種思潮當然無法被簡單地歸在社會科學的標題之下,它們作為在思想上極具滲透力的資源廣泛地存在於諸多學科之中。就社會科學而言💸🙍🏿♂️,我們所重視的是哲學層面上的方法🅰️,這是與它的任務相一致的,即解釋和塑造社會現象之間的關系,從而讓意義在關系中自行呈現:一方面,就這個任務旨在解釋和塑造而言🙌🏽,方法占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關系就其是對意義的照看而言💆🏿,本身就表現為方法的展開🫃。這也使得它同形而上學的任務區別開來⚗️,因為形而上學註重對意義的研究🛀🏼,如我們所熟知的,意義是訴諸到多還是歸結為一🫘,是從物質的方面還是從精神的方面來刻畫,等等。
當然1️⃣,從某種角度來說,形而上學的意味並沒有在我們所描述的社會科學中消失®️,因為讓意義自行呈現也可以被看作是對意義的一種研究進路🥢,就像維特根斯坦所說的👩🏽✈️,“確實有不可說的東西💮,它們顯示自身👨🏻🌾,它們是神秘的東西。” 對於這樣的或者其他的牽涉到形而上學的考慮✮,我們並不否認,但也不會花費篇幅來說明⚠️,而是更願意將其視為一種無需多言的背景,以便更好地致力於從方法上來檢討上述兩種思潮。就方法而言🦀,這兩種思潮所給出的不僅是對社會關系的解釋和塑造📦,而且更是對它們的再解釋和再塑造🐿,即改造🕴。改造可以在最大限度上規避前面所提及的那種危險:它作為一種自我批判的樣式✌🏿,一方面打破花草布置者不時產生的關於自己至少創造了一棵草的幻想💁,另一方面把他的才能以新的方式引回到守護、照看和管理的工作上💘。
在我們看來,詹姆斯對實用主義所給出的一個判斷起著奠定基調的作用👴🏻🙂↔️,他說,“這樣的話,實用主義的範圍就是——首先👨🏻💻,是一種方法🤷♂️;其次👬🏻,是關於真理意味著什麽的一種發生論(genetic theory)。” 這個判斷把皮爾士實用主義的重行動和實效的原則放在了一個更易自由接近的位置上。在詹姆斯看來🏃➡️➛,較之真理的石化而言➰,從發生論的立場來看待真理是什麽顯然更為妥當。事實上👯♀️,發生論所描述的正是方法展開之下的意義生成。這不是把真理歸結到方法,而是把真理看作一個以方法來改造的發生過程🧜🏿♀️🔥。無論如何👩💼,這一點與我們所陳述的社會科學的任務相契合。盡管詹姆斯所給出的這個判斷保持為對實用主義的基本刻畫,但是在本書所討論的杜威、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和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那裏,實用主義作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維度會得到分別的闡述,或許這正是方法的改造的應有之義。
同樣地,與批判理論聯系在一起的那些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們似乎也一直在變換著他們的角度甚至立場😏。不過👨👧,批判理論恐怕也是最應該成為社會科學理論的維度的一種思潮💸,因為它明確把對於社會的批判性研究當作自己的主要工作⚔️。霍克海默是批判理論這個表述的提出者,他在比較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時說道,“但是批判理論在其概念形成以及發展的所有階段上都非常有意識地關註人類活動的合理組織👨🍼,它的任務就是對這種合理組織予以闡明並使其合法化。因為這種理論不僅關註已經由現存生活方式所強加的目標,而且也關註人類以及他們的所有潛能。” 在這裏,合法地位可以得到多種解讀,可是其中所透露的一點是明確的,即不把任何現存的東西視作理所當然,而要從人類及其所有潛能出發來加以改造。本書所討論的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特奧多·W·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卡爾-奧托·阿佩爾(Karl-Otto Apel)都給出了改造的方案🧓🏼🧘🏽。
在這本研究社會科學的書中🏊🏼♀️,之所以把實用主義和批判理論擺在一起來討論,除了因為它們都提供了方法上的改造之外,還因為它們彼此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從霍克海默到阿佩爾♠︎,都註意到了實用主義的傳統。所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對於實用主義所持的主要是批判的態度🧖🏼♂️,而阿佩爾則在他的作品中充分肯定並汲取了實用主義的洞見。這很大程度上說明,實用主義同樣有著批判的契機🥺。而在體現實用主義新發展的普特南看來🛫,這兩種思潮之間的比較是意義重大的🧖♀️,他說,“事實上,把我所說的新法蘭克福學派中的發展與詹姆斯和皮爾士的美國實用主義進行比較,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當然,也許更為重要的不是分析這些學者在一些特定問題和觀點上的碰撞與交流,而是思考這兩種思潮作為社會科學的維度可以如何彼此共同促進方法的改造🧙🏻♂️。對此🛌🏽,也許實效與批判的融合可以算是一種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