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震著作集·陽明學系列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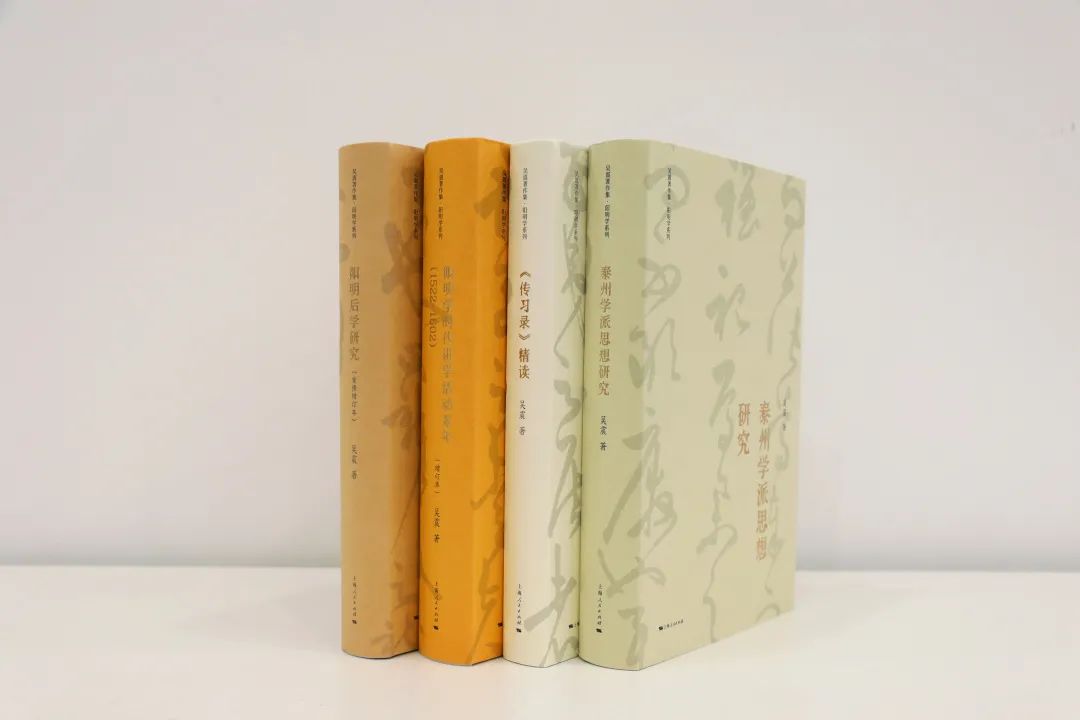
《陽明後學研究(重修增訂本)》
《〈傳習錄〉精讀》
《陽明學時代講學活動系年(1522—1602)(增訂本) 》
《泰州學派思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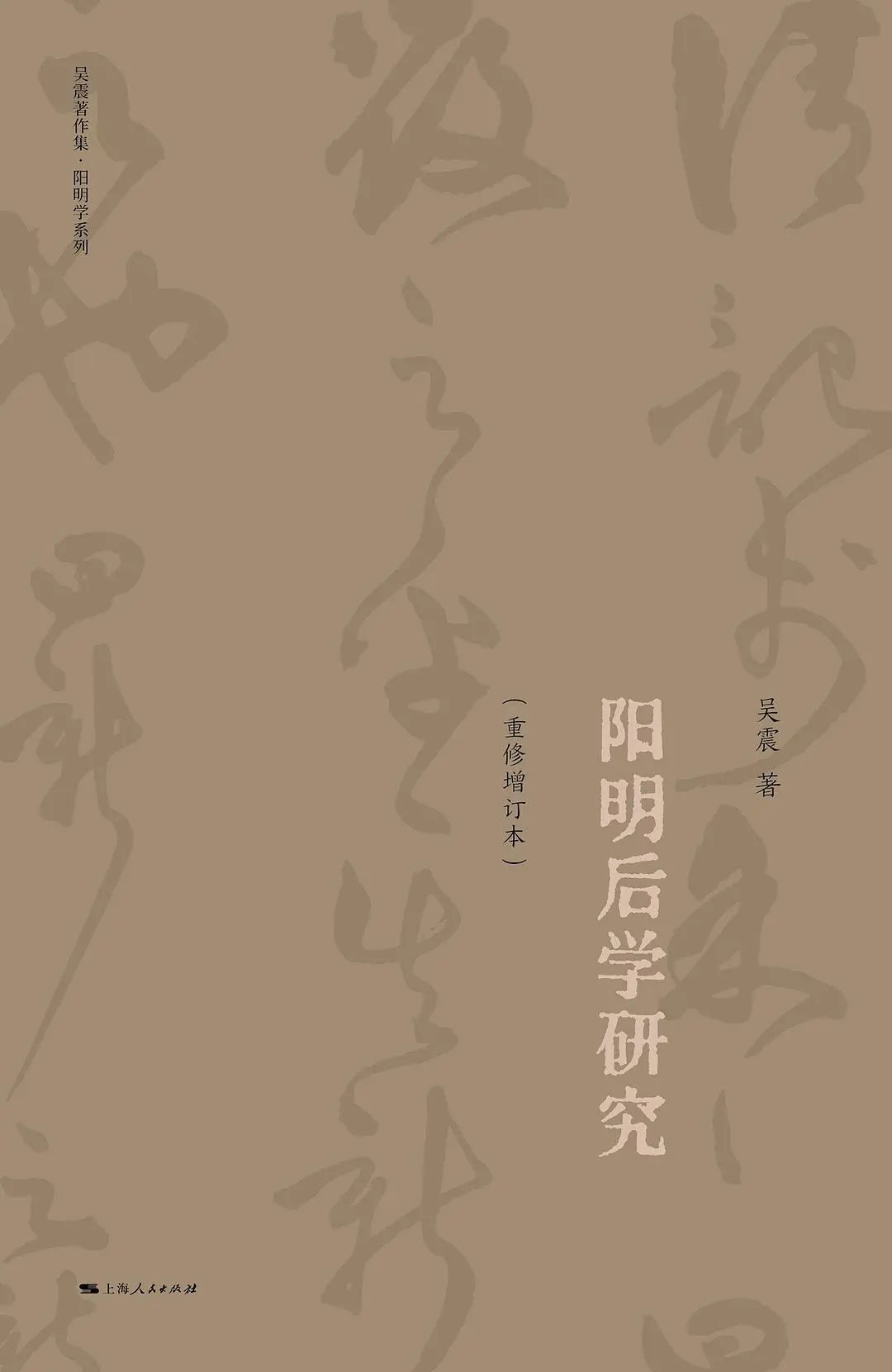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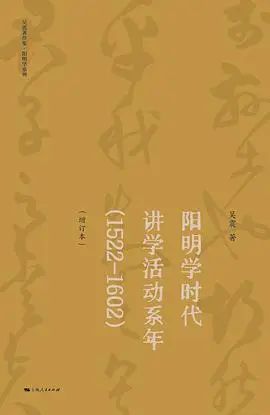

作者:吳震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年2月-2023年3月
吳震🤜🏻,意昂3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意昂3平台上海儒意昂3執行副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儒學研究會會長🏋🏻、國際儒聯理事暨學術委員會會員等。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哲學🗃、宋明理學、東亞儒學等。主要著有《陽明後學研究》(2003初版、2016增訂)、《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系年:1522—1602》(2003)🦇、《泰州學派研究》(2009)、《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2009初版👷🏽♀️、2016修訂)🦍🍞、《〈傳習錄〉精讀》(2011)、《當中國儒學遭遇“日本”——19世紀末以來“儒學日本化”的問題史考察》(2015)、《顏茂猷思想研究——17世紀晚明勸善運動的一項個案考察》(2015)、《東亞儒學問題新探》(2018🛌🏻🚴🏽♂️、韓文版2022)🫰🏻📢、《朱子思想再讀》(2018)、《中華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傳習錄》(2018)、《孔教運動的觀念想象——中國政教問題再思》(2019)🕵🏻♂️、《朱子學與陽明學——宋明理學綱要》(2022)等;主編有《宋明理學新視野》(2021)、《視域交匯中的經學與家禮學》(2022)等。
值次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我的“著作集”四書之際,需要寫篇總的《後記》,講一下這幾本書的成書過程以及修訂情況。
1982年我在復旦哲學系攻讀中哲碩士學位時,就開始從事陽明學特別是陽明後學的研究👐🏿,至今正好是40年。1980年代末進入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後期課程,更是將精力集中在陽明後學研究領域🕵🏿♂️,並以此為題提交了學位論文📡。此後經過翻譯、修訂、增補的漫長過程,同名博士論文《陽明後學研究》終於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迄今將近20年👵🏻;十余年後又經較大幅度的修改增訂,同在該社刊行(2016)🪬。若再加上《明末清初勸善運動思想研究》(修訂版)在該社的出版(2016)🆗,可以說,我的學術著作跟上海人民出版社有著很深的緣分。這次該社推出我的“著作集”,以“陽明學系列”命名,收入四部有關陽明學的研究著作🤲,於我而言,這是莫大的榮幸,也是對自己40年來學術研究生涯的一個總結。
《陽明後學研究》(以2016年增訂版為例)共分九章👳🏽,主要以人物個案研究為主,涉及王龍溪、錢德洪、羅念庵、聶雙江、陳明水、歐陽南野🧑🚀、耿天臺📘,其中,念庵和雙江是從舊著《聶豹·羅洪先評傳》(2001)中抽出☮️,龍溪😸、德洪👷🏼♀️、天臺三章則在日本留學時已作為單獨論文發表,這些人物個案的研究在當時大陸中國哲學界尚屬首次。只是王龍溪一章的研究偏重於其思想與道教的互動問題,未涉入其心學理論本身𓀗,這是由於序章“現成良知”和第一章“無善無惡”(先後發表於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4期🖌,商務印書館2000年👵🏼🧪;《中國學術》第13期,商務印書館2003年)這兩章不同於人物個案研究而是以問題史考察為重點,幾乎就是以龍溪思想為核心而展開的。自龍溪指出“先師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見在而言”,“見在良知”或“現成良知”的問題便成為王門爭辯的核心議題,形成了各種王門良知說🤳🏿,而龍溪推演陽明晚年“四句教”而得出“四無說”的觀點,更是在王門以及晚明思想界引發了聚訟紛紜的激烈爭辯🛟,可以說在陽明學的發展史上,龍溪思想是理解陽明學的重要參照坐標🏤,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此次收入“著作集”,刪去附錄“心學道統論”一文,新增“王時槐論”一章🙌,該文原是《聶豹·羅洪先評傳》中的附論,也應算作當時研究陽明後學的成果之一🏋🏽。
在《陽明後學研究》出版同年,學林出版社刊出我的另一部書《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系年:1522—1602》,為配合本“系列”名稱,特將“明代知識界”改為“陽明學時代”♢。在該書初版《後記》中,我曾說這本書其實是我研究陽明後學的“副產品”,這是實話。但正由於是“副產品”,所以不免受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原始文獻資料尚未大量刊行出版的局限🐨,迫使我的資料收集采用了近乎“手工業作坊”的方式,全靠平時跑圖書館得來🧘🏼♂️,雖不至於“上窮碧落下黃泉”,但確實做到了“動手動腳找材料”(傅斯年語)。然後通過閱讀整理,累積起數十萬字晚明士人社群(以王門為主)推動講學活動的資料,才有上述《系年》之作。時過境遷,21世紀的當下,不僅明代文獻的整理出版有了爆發式增長🚿,而且可以憑借電子人文技術,坐在電腦前就可從各種文獻資料庫瞬間獲取大量的古籍文獻資料。在如此優越的條件下🧏🏻♀️,按理對這部舊著應作全面的修訂💊,然而近年來科研教學等各種事務纏身🕊,其壓力之重,想必在學術圈內者可以諒察,這導致我根本無法抽身進行修訂。幸運的是,素昧平生的江蘇師範大學蘭軍博士熱衷於明代講學活動的研究,經人介紹⏺,他自告奮勇承擔了《系年》的全面修訂工作🤒,並新增了近8萬字的材料💂🏻。所以在此必須鄭重地向蘭軍博士表示衷心感謝!不過需要說明的是,蘭軍博士新增部分大多是根據“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等新出的各種標點本進行收集整理的,與我的原著主要使用原刻本不同♋️。
《系年》一書關註16世紀20年代以降八十年間🙆🏿♂️,以陽明後學為主的士人社群如何積極投身社會講學的活動狀況☝🏼,而這場講學運動具有跨地域以及超越身份限製的特征,通過儒家精英的這些講學活動使得儒家經典知識得以轉化為士庶兩層社會都能普遍接收的常識🏌🏻♀️,加速了儒學世俗化的轉向;同時也使我們發現那些心學家投身講學表現出某種宗教傳教士一般的熱誠👩🏽🦳5️⃣,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在他們的觀念中,有必要重新接續孔子“席不暇暖”從事講學的思想精神👩🏻🚀,而儒家講的“萬物一體之學”更有必要轉化出“萬物一體之政”,並通過“政學合一”的互動方式來推動社會秩序的重建。質言之❌,陽明心學倡導個體精神的自我轉化只是初級目標,通過自我轉化以推動社會轉化👩🏽🦰👩🏻✈️,並使這種雙重轉化得以同時推進👳♀️,以實現社會轉化和秩序安定,才是心學理論乃至儒家思想應追求的終極目標。
《泰州學派思想研究》(收入吳光主編“陽明學研究叢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原書名無“思想”兩字)是我研究陽明後學的最後一項計劃,至此🏬🤐,我對陽明後學的三大板塊:浙中📼、江右、泰州的研究,總算告一段落🙌🏻。緒論“泰州學派的重新厘定”對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所設立的思想標準進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黃宗羲一反其設計六大“王門學案”的標準——即以地域出身和師承關系為設準,在“泰州學案”的設定中,他將出身地域不同👨🏿🏫、又無明確師承關系的一些人列入“泰州學案”,遂致整部“學案”成了一鍋“大雜燴”😅🧑🏿⚖️,李卓吾且不論🈶,因為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完全無視他的存在,姑就泰州學案所列的趙大洲、耿天臺、管東溟🏎、周海門等人物思想來看,他們何以跟王心齋開創的泰州學派有關是令人懷疑的🐈⬛💤。在對“泰州學案”作出重新厘定之後,我將視角集中在王心齋🛣、王東厓🕐、王一庵、何心隱🤷🏽♂️、顏山農、羅近溪六人身上,著重探討了心齋和近溪,其中心齋雖只占一章,然此章篇幅長達全書三分之一強,近溪一章大約占了四分之一,這是從《羅汝芳評傳》(2005)中抽出的🦠。趁此次新版,增加一篇前年所作《“名教罪人”抑或“啟蒙英雄”?——李贄思想的重新定位》(《現代哲學》2020年第3期)一文,庶幾可為泰州學派研究畫上句號。盡管李贄算不上泰州學派中人🙅🏽♂️,然通過對其思想的定位,或可為我們重新觀察泰州學派提供另一條思路🧑🧒。我的看法是☝️,罵李贄為“名教之罪人”(於孔兼語)、對泰州學人作出“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黃宗羲語)這類“定讞”式的判語,這不過是儒家精英對活躍於底層社會的民間儒家學者所顯示的一種傲慢,並不意味著泰州學人真有反儒學、反傳統的所謂“啟蒙精神”🛀。
《〈傳習錄〉精讀》是我1999年為博士生開設“傳習錄精讀”課程的講稿👩🏼🦱,後經反復講述和文字修訂,由意昂3平台出版社刊行於2011年。不知何故,出版之同年便連續印刷四次💽,此後由於所謂“電子書”悄然上市🧗🏻♀️,該書就再也沒有了加印或重版的機會。其實,這部講稿並不算通俗性讀物✣,盡管在講述時需要考慮基本知識的普及,但重點卻放在對陽明心學思想體系的深入解讀🧑🦳,因而打亂了《傳習錄》文本條目的次序,將其納入到陽明學的思想結構中進行了重新組合,目的在於揭示陽明學的義理構架及其思想內涵📋。因而題名中的“精讀”只是意指通過對《傳習錄》的深入解讀,以展示陽明心學的哲學意義及其所蘊含的“問題”。此次收入“著作集”,另增兩篇近年寫的文章《論王陽明“一體之仁”的仁學思想》(《哲學研究》2017年第1期)和《作為良知倫理學的“知行合一”論—— 以“一念動處便是知亦便是行”為中心》(《學術月刊》2018年第5期),以圖本書的陽明學研究得到進一步充實📒。
以上四書收入我的“著作集”之際,未作任何文字的修訂,新增幾篇附錄及相應的篇幅調整,已如上述✋🏻。各書的文字校對則由蘇杭博士後、郎嘉晨、崔翔博士生以及範旭和曹宇辰碩士生代勞☀️,對於他們的辛苦付出,我要表示感謝😸!雖然各書原有的《後記》被一並取消,但其中寫下的“鳴謝詞”則永遠有效。最後衷心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社長、現任上海市社聯黨組書記王為松先生,承其關愛,本“著作集”才得以問世;感謝上海人民出版社趙偉🕘、任健敏等編輯朋友🔙,使我很榮幸能將自己近四十年來的陽明學研究之成果奉獻給廣大讀者💇🏽👩🏽🍼。
吳震
2022年11月18日